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研院史語所研究員)
自簡牘帛書的研究成“學”以來,簡牘的重量和體積似乎是一個還不曾被討論過的問題。這個問題看似無關宏旨,其實關係不小。以下不妨從一個東方朔的故事說起:
朔入長安,至公車上書,凡用三千奏牘。公車令兩人共持舉其書,僅然
能勝之。人主從上方讀之,止,輒乙其處。讀之二月乃盡。詔拜以為郎。
(《漢書•滑稽列傳》東方朔條)
東方朔上書,用牘三千,公車令二人勉強搬動,進呈武帝。三千奏牘堆疊起來體積龐然,奏牘起首的部分顯然堆在上層;武帝從上方讀起,兩個月才讀完。班固在東方朔傳贊裡說他的滑稽故事多不可信,須特別花功夫甄別,可信的才入傳。三千奏牘一事不論是否可信,無意中透露竹木簡牘的重量和體積,不論在搬動或閱讀上,可以造成習於用紙的今人難以想像的問題。學者早已利用這個故事中“乙其處”之語,說明古人閱讀時的注記習慣,卻忽略了這三千奏牘重量和體積的意義。[1]重量和體積如何左右文書的形式、存放和管理,就“簡牘文書學”或古代文書檔案管理研究而言,不能不說是一個基本課題。
一.史語所藏簡牘重量和體積的測量
近數十年來,中原地區出土很多戰國或秦漢簡牘,出土時多泡水,為保存不得不脫水和用藥劑處理。重量和體積都因而發生變化。居延和敦煌出土的簡牘情況不同。這些木質為主的簡牘保存於沙土之中,因長期乾燥,重量雖或變輕,畢竟大致保持原狀。
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有一九三○年代發掘的一萬餘枚居延漢簡。其中十餘枚為竹簡,餘為木簡。史語所漢簡整理小組過去曾全面整理,測量了簡的長寬厚,唯未留意重量。目前整理小組已經解散,一時無法再進行全面測重。去年(二○○五)底和今年初,我利用機會抽樣測量了少數簡。現在將測量數據公佈(附表一~三),供大家參考。
測量樣本中較重要的是兩件完整的簡冊。史語所珍藏編繩和編簡都完整的簡冊兩件,一件是由三簡編聯而成的57.1號簡冊,另一件是128.1號由七十七枚簡編成,迄今最長的漢代簡冊,也就是通稱的永元器物簿(附圖1.1-4)。這兩個簡冊除了編聯簡數和長度不同,基本形制一致:第一,使用的簡都是長約23公分或漢一尺,寬約1公分,厚約0.2-0.3公分的典型木簡;第二,編法上都使用兩道編繩,簡側都沒有契口。漢代文書的重量,除了簡本身,還有編繩。絕大部分漢簡都失去了編繩,即使簡冊得以復原,整冊的重量仍不易準確估計。因此這兩件帶編繩簡冊就特別有意義了。
兩件簡冊在史語所陳列館中長期展示。二○○五年十二月廿六日因調整展櫃,展件暫時送回中原考古庫房。我得到庫房林玉雲小姐的協助,於廿七日上午在倉庫第一次對這七十七枚組成的文書冊進行測重。測重工具是一台專供實驗室使用,靈敏度極高,美國Denver Instrument 公司生產的XJ-2100型電子磅秤。秤得重量為243.63公克。這包括七十七簡和所有的原編繩。
為了安排攝影,到二○○六年一月三日上午才又測量128.1簡冊體積。單簡一枚長23.3-23.5公分,寬0.7-1.3公分,厚0.2-0.3公分。簡冊的簡體部分(不包括一側多出的編繩)全長90公分。原簡冊上附有一條紮繩,一頭打有兩個結。我們沒有解開結,現有紮繩長度展開後長57公分。
因為想知道簡冊捲起後的體積,林玉雲和我曾將128.1號簡冊捲起來。我們從文書開頭的一端開始。這是考慮到整組簡冊是由三組不連續的編繩編聯在一起,尾端有相當長多餘出來的編繩,可供繼續編聯之用;簡冊捲起時,留有多餘編繩的尾端原應在簡冊的外層較為合理。[2]當然不論從那頭開始捲,都不影響重量和體積的測量。捲好後,整個成捲的簡冊從一頭看,有些扁塌,呈橢圓形。上下直徑為7.5公分,左右直徑為9公分,平均8.25公分。有了長度和直徑,這一捲簡冊的體積即可大致估算出來,在1250立方公分左右。
57.1號簡冊由楊德禎小姐於二○○六年一月九日測重,三簡加編繩共重11.38公克。如果拿這三枚簡的簡冊和128.1簡冊的重量比較,可以發現128.1號簡冊一簡加編繩平均約重3.16公克,而57.1號簡冊一簡加編繩平均約重3.79公克。如果將兩件簡冊共一百簡(77+3)加編繩的重量平均計算,則一簡加編繩平均約重3.19公克。木簡重量因質材、厚薄、長短、寬窄頗有差異。我們曾任取形式一致,簡體完整,各書寫一行字的八枚簡作為抽樣樣本,測量結果長度在22.6至23.7公分之間,寬在0.9至1.4公分之間,厚在0.24至0.53公分之間,平均重量為4.035公克(附表三)。換言之,這八枚簡的平均重量反而在上述兩簡冊帶編繩各簡的平均重量之上。影響重量差別的一項因素是木材種類;種類不同,木材重量差異頗大(附表四)。
此外,同樣大小的竹簡和木簡,重量並不一樣。這有兩點必須考慮:第一,不同的竹木材質原含水分比例應有不同,分析竹木簡重量應考慮竹木的品種;第二,目前掌握的樣本經過二千多年乾燥,早已脫去不同比例的水分。除非經由實驗,找出竹木脫水比例常數,否則難以完全準確地復原原重量。
史語所藏居延漢簡中有少數為竹質,我們挑選了形式一致,基本完整的漢尺一尺的竹簡十二枚測重。每枚重量輕則1.59公克,重則5.03公克,差別不小;十二枚平均約重2.616公克(附表二),而木簡則平均重4.035公克(附表三),木簡明顯較寬、較厚,也較重。一枚木簡之重約是竹簡的1.54倍。不過這並不表示新製好的竹木簡在重量上有這麼大的差別。可惜我們沒有設備和人力作進一步更精細的測定。
為了能作些初步實驗,二○○六年七、八月間隨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組織的考察隊到居延漢簡出土的額濟納河沿岸考察,我刻意尋找了漢簡主要的木料來源-胡楊和紅柳。在額濟納河沿岸仍生長著成片的胡楊林或零星聳立在大片黃沙中的胡楊樹,在戈壁上和遺址旁則不時見到零散分佈的紅柳叢。我採集了木料標本,注意到胡楊枝榦雖較粗較高,木質遠較屬灌木類的紅柳疏鬆。紅柳枝榦質地極為細密堅實,相對重量要比胡楊重得多(附表四)。同樣大小的木簡如果用胡楊或紅柳製成,即使經過乾燥,重量相差很多。額濟納河一帶目前已見不到松樹。居延漢簡有不少松木製的。這次在漢代遺址中拾到一些松木標本。松木木紋清晰,和胡楊、紅柳十分不同,不難辨別。松木質地較接近胡楊,不如紅柳堅實,重量也明顯較輕。
回台後,請人將胡楊、紅柳和松木標本依漢簡的一般長寬厚(23.13×1.18×0.34公分)切割成簡。紅柳標本是我用小鋸自紅柳樹上鋸下。胡楊標本因胡楊樹太高,最低的樹枝都在一人伸手所及的高度之外,只能撿拾地上斷落的枯枝。松木標本是自遺址中撿拾而來。因額濟納河當地已無竹子,我用台灣所產新鮮未脫水的竹子作成同樣長寬厚度的簡。這些標本簡因本身材料性質不盡一致,乾燥程度不同,由此得來的數據並不能符合嚴格的實驗要求。這是必須聲明的。此外,還有一點必須說明,切割竹木簡時雖用了較精準的雷射刀鋸,希望切成的長寬厚度儘可能一致。事實上,因為材料的軟硬和紋理曲度,切出來的每一簡在長寬厚上仍有些微差異(附表四)。因此,重量和體積僅能以平均值作相對性的比較。也由於這一番切割的經驗,才知道古人沒有近代工具,要製作出光滑平整,大小厚薄一致的木簡,尤其如果是紅柳木,很不容易。以竹木簡的切割相比較,由於紋理性質不同,相對而言,切削竹簡要容易得多。[3]
二.古代簡冊與書籍重量估計
居延邊塞出土的這些簡和編繩因長期乾燥,其重量理論上應較原本為輕;輕多少?仍待比對研究。如果以128.1號簡冊的重量為準,又如果東方朔不用牘而用簡,三千簡大約重9,491.825公克,或9.5公斤左右。如以以上兩件簡冊的平均重量3.475公克一簡為準,則三千牘就有10,425公克,稍多於10公斤。如以上述八枚簡的平均重量4.035公克計,則三千簡達12,105公克,即12公斤餘。9.5~12公斤不算太重,一二人即足以抬起。
如果東方朔是用較簡為寬的木牘,三千牘的重量更要多上好幾倍!漢代一般稱寬木簡能容好幾行字的為牘,其寬窄厚薄不很一致。以這次抽樣者為例,牘輕者一枚不過4.86公克(26.21),重者一枚達21.81公克(286.19、562.1),折中而計,一枚也有13公克餘。如此東方朔的三千牘可重達三十九公斤!
另外舉個例子來說。司馬遷所撰《史記》既不是經書,也不是詔書或律令,依漢代的習慣,書寫用的簡當為一般漢一尺或約二十三公分長的竹木簡。《史記》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須要多少枚竹或木簡來書寫呢?可以粗略估算。目前所見一般簡上書寫字數因單行或雙行書寫,可容十或二十餘字,甚至上百字。[4]這裡姑且以與司馬遷時代較近,內容性質也較接近的江蘇尹灣東海郡功曹史師饒墓中所出《神烏賦》竹簡為參照。《神烏賦》竹簡長約二十二至二十三公分,單行書寫,每行約三十三至四十三字,平均三十八字左右。山東臨沂銀雀山西漢初墓出土的幾種典籍竹簡如《孫臏兵法》長約二十八公分,每簡書寫字數也在三十五至三十八字左右。假設《史記》以同樣的形式書寫,一簡以三十八字計,則須竹簡13,855枚,是東方朔奏牘數量的4.6倍,以木簡的重量計,則達43.7~48.1公斤,甚至55.9公斤。如以新鮮的竹簡計(參附表四:竹簡重量平均值),則達58.33公斤;用新鮮紅柳簡則更重達101.62公斤!不過司馬遷著述於長安,所用似較可能為竹簡。近年出土戰國至秦漢簡,其非出於邊塞者,雖有木簡,一般多為竹簡。[5]要抬起或移動這樣一部四、五十公斤的《史記》,比東方朔的三千奏牘,更為勞師動眾。
相對而言,真正造成困難的應在體積。體積之龐大會造成搬運、貯藏和管理上的問題。前文提到我們曾將七十七枚簡組成的128.1簡冊捲起來,試圖知道這樣的簡冊體積多大。因為深恐造成損害,捲的時候不敢太用力,另一方面因為麻質的編繩有一定硬度,無法捲得很緊。或許因為不太緊,捲起來以後,置於桌上,成捲的冊子上下較扁塌,直徑約7.5公分;左右較寬,直徑約9公分(附圖1.4)。如果取平均值8.25公分當直徑,就可以估計出此簡冊成捲的體積約為1250.877立方公分(4.125²×π×23.4)。考慮到這些簡冊捲起來排放在一起時,各捲不可能完全緊密,了無空隙;一捲所佔的空間實際上是簡冊長寬高之積。如此一來,其體積應在1579.5立方公分左右(7.5×9×23.4)。如果七十七枚簡冊所佔空間為1579.5立方公分,以13,855枚簡抄成的《史記》,其體積約達一百八十倍,即284,310立方公分左右。
284,310立方公分意味著多大的空間,不容易想像,但可作一個比較。我手頭有一部藝文印書館景印乾隆武英殿刊本,包括裴駰《集解》、司馬貞《索隱》和張守節《正義》在內的精裝《史記》兩冊,疊在一起長寬厚共為26×19×6=2,964立方公分。換言之,漢代一部竹木簡抄寫的《史記》本文,體積上約為現代含三家注本《史記》的九十六倍!武英殿刊本包含的三家注印成雙行小字,字數似乎沒人統計過,但肯定比《史記》本文多。現在已很難找到沒有加注的《史記》白文本。幸好司馬遷曾精確地說他的《史記》有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五十二萬餘字的書如果以北京中華書局點校本二十五史的版面形式印刷,一頁印五百六十字,約須九百四十頁,體積恰好和中華點校平裝本三冊《周書》相近(15×21×4=1,260立方公分)。如果僅計白文,漢代竹木簡本的《史記》體積是現代紙本的二百二十五倍! 也就是說,現在在書架上放一部不含注解的《史記》白文,在漢代就須要最少二百二十五倍的空間。
三.檔案保存與維護
《史記》一部不過一百三十篇,《漢書•藝文志》著錄的漢代圖籍共達一萬三千二百六十九卷。《抱朴子外篇•自序》說劉向《別錄•藝文志》“眾有萬三千二百九十九卷”。姑不論準確的卷數和每卷的大小,這些都是劉向在長安未央宮秘府校書時見到的書。這些秘府圖籍並不包括漢代中央政府的公文檔案。我們已無法知道這些檔案有多麼龐大,顯然要比秘府圖籍龐大得多。僅以法律文書來說,《鹽鐵論•刑德》謂:“方今律令百有餘篇,文章繁,罪名重…律令塵蠹於棧閣,吏不能徧覩。”《漢書•刑法志》說武帝時:“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一事。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這僅僅是律令。日常中央及地方各單位往來行政文書數量必更為驚人。依漢代之制,公文書除起草和送出的正本,各相關單位還要抄錄副本。其中有些固然定期銷毀,[6]有些如“故事”則須長期保存。由此不難想見中央各府寺行政文書的數量必遠遠在蘭台和秘府等收藏的經史典籍之上。
從可考的藏書處來說,西漢武帝以來,天下獻書,“外則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內則有延閣、廣內、秘室之府”(《漢書•藝文志》如淳引劉歆《七略》),此外還有蘭台、石室、石渠閣、麒麟閣、天祿閣。(《三輔黃圖》卷六;《漢書•儒林傳》施讎條師古曰引《三輔故事》)東京以降除南宮,有蘭台、石室、辟雍、東觀、宣明、鴻都等藏書閣。[7]東觀“在南宮,高閣十二間”(徐松《河南志》卷二引陸機《洛陽記》)這些地方或藏舊典,或藏公文檔案,其規模必不小。另有些貴重的策命之詔、謚號之策、盟誓之丹書鐵券、封禪之玉版等等並不藏在尋常的藏書閣,而是藏於宗廟或宮室。[8]可惜長安未央宮雖經發掘,未央宮北的天祿閣和未央宮前殿西北石渠閣遺址也被指認出來,它們的繁華盛大,已不易從殘存的基址去想像了。[9]
更難想像的恐怕是這些文書如何分類,如何排放,又如何在須要查看時找出來。這和行政效率直接相關。據文獻可知,有些簡牘文書是盛於以織物製成的書囊裡。[10]據出土實物和簡牘文書,則知為了儲存或傳送,簡帛文書又會裝在竹笥之中,如馬王堆漢墓出土之竹笥,竹笥之外還有繫繩和封檢。這些竹笥應該就是文獻中所說用以盛書用的“筐篋”之類。賈誼說:“俗吏之所務,在於刀筆筐篋”,師古曰:“筐篋所以盛書。”(《漢書•賈誼傳》,頁2245)賈誼和師古之說可以從張家山《二年律令》得到印證。《二年律令》〈戶律〉曾提到宅園戶籍、年細籍、田比地籍、田命籍和田租籍這些重要的籍簿要在縣廷保存一份副本,“皆以篋若匣匱盛,緘閉,以令若丞、官嗇夫印封,獨別為府,封府戶”(簡三三一.178~三三二.178)云云。我們或可想像在存放文書的“府”中,盡是一排排封緘過的筐篋。如何排放?幾無可知。在文書分類上,從“令甲、令乙、令丙”、“天子所服第八”、“蘭台令第卅三”、“御史令第卌三”、“某年某月盡某年某月吏病及視事書卷”、“某年某月至某月吏寧書”這些大家熟知的線索可約略見其梗概。
關於如何排放,所知甚少。“律令塵蠹於棧閣”、“文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之語則反映檔案龐大所可能造成查找的困難,也反映文書是藏於所謂的“棧閣”或“几閣”。棧閣和几閣是什麼樣子?按《說文》,棧是棚,几是踞几,應是矮桌。宋代文書存放有所謂“架閣庫”,架閣指存放文書,內分數十個抽屉匣的櫃架。[11]宋代文書是紙,用紙以前呢?除了棧、几、閣,幾無線索,研究也少。[12]十分期待今後考古工作不但能注意搶救簡帛,也能注意簡帛出土的環境和原本的存放狀態。例如漢長安未央宮遺址曾出木簡,也曾出數萬件認為是“檔案”性質的骨簽,如果發掘時曾仔細留意它們原本排放所留下的痕跡,找到可以復原的線索就好了。[13]
以下僅根據一點點的線索,說明簡牘存放除了几閣,可能也分類懸掛於壁。大家都知道崔寔《政論》曾提到“州郡記,如霹靂,得詔書,但掛壁”(《太平御覽》卷四九六,頁2397-2;卷五九三,頁2801-1)。詔書如何“掛”法?令人好奇。首先請注意幾件較完整的簡冊,其編繩末尾有打結成圈環的現象。例如史語所藏永元器物簿冊末尾兩道編繩各結有一個圈環(附圖2)。肩水金關出土“勞邊使者過界中費”冊以九枚簡,兩道編繩編成,冊左側編繩稍長,打了結,留下圈環。[14]這種情形也見於近年新刊佈的額濟納漢簡“專趣士吏典趣輒”冊。此冊有八簡,兩道編繩右側起頭處留下了兩個圓圈環。冊尾編繩也打了結,但繩末開口,應可繫楬。[15]這些圈環的作用引人注目。我猜想就是供懸掛時之用。壁上有釘,即可懸掛。“專部士吏典趣輒”冊兩頭都有圈環,可以平掛,便於閱讀,或應如胡平生所說,是所謂的“扁書”。[16]其它只有一側有圈環,只能豎掛,不便閱讀;這樣的懸法,自然不是為了閱讀,而是存放。“得詔書,但掛壁”就是將詔書往壁上一掛,存檔了事的意思。《中國畫像石全集》第三冊收錄臨沂白莊出土一石,其上有人手持編簡,壁上有懸掛的簡冊(附圖3)。[17]由於刻工細緻,可以清楚看見懸於壁的簡冊帶有編繩,而且是豎掛。我推測簡冊如果分類掛懸,不失為一種不同於紙本文書的存放方式。目前還沒有分類的證據,但懸掛簡冊,於漢代的確有文獻和圖像可證。
前引《鹽鐵論•刑德》說“律令塵蠹於棧閣”,這就不禁使我們想到保存檔
案在“塵”和“蠹”兩方面的維護問題,以及竹木質之物最怕的火災問題。為防塵,一般置於囊或筐篋之中;為防蠹、防霉或又為易於受墨,從若干出土簡(如長沙走馬樓簡)已知古人在製簡的過程裡,會在簡面塗刷一層至今不明的油性或膠性物質。[18]
為防火,睡虎地秦律〈內史雜〉規定不准將火帶進收藏物品的“藏府”和收藏文書的“書府”,其近旁也不准興建吏的居舍。[19]漢代會預備井和水缸(滅火水缸見望都一號漢墓壁畫,水缸榜題“戒火”二字)等滅火之具,也會繪製象徵水,起厭勝作用的的荷、菱於建築的藻井或“厭火丈夫”於牆上。[20]這樣的防護措施當然也用於一般建築。可能也是為了防火,才會將一些較為貴重的文件放置在所謂的石室金匱之中。
四. 和體積、重量相關的使用問題
在重量和體積上,竹木簡牘雖較古代兩河流域所使用的泥版輕便耐用,較古代埃及的莎草紙(papyri)或中國魏晉以後流行的紙,則遠為笨重龐大。這樣的文書載體如何影響到官僚行政的效率和管理,又如何影響到知識、文化的傳播,文化品味和藝術的產生(如漢末魏晉以降紙的流行和書法、繪畫藝術的興盛),都是有待進一步研究的問題。這裡先僅就思考所及,提兩點和漢代典籍、文書管理以及簡冊制度相關的想法:
1.檔案定期銷毀
汪桂海先生從漢簡文書內證,證明漢代有文書定期銷毀制度,一般文書約十至十三年即銷毀。[21]從竹木簡牘文書的體積和重量,可以旁證其說有理。竹木簡牘文書體積龐大,如果長期累積,不加銷毀,儲存空間必然成為問題。
文書定期銷毀制在用紙時代開始以後繼續存在,但在使用竹木簡牘的時代,銷毀的迫切性似乎要更高。據《唐律疏議》,唐代文案分為應除文案和見行文案,凡“不須常留者,每三年一揀除。”凡揀除淘汱者為應除文案,常留者為見行文案。《宋刑統》和日本《養老公式令》也有三年一揀除的規定。[22]據研究,宋代一般官文書保存以十年為期,每三年“檢簡”或鑒定一次,凡須永久保留者移至別庫架閣,否則定期銷毀。[23]漢代一般文書是否能有十年至十三年的保存期?比宋代紙文書保存還長?不無問題。漢代邊塞文書雖然繁複龐雜,其數量恐怕還遠遠比不上中央各府寺或地方郡縣。漢代中央或地方郡縣一般公文書能保存多久?幾無資料可考。我估計除了永久保存者,一般保存期限恐怕很難比唐或宋代更長。
此外,似乎也必須考慮到秦漢時因使用竹木簡,迫於體積和重量,對文書的存毀應有比十或十三年期限更細密的規定。也就是說,對不同性質或內容的文書,應有更多保存期限等級上的規定,而不是僅分為一般和永久兩類而已。
再者,銷毀的意義也有多種,不一定只靠定期銷毀。為充分利用資源,漢代邊塞吏卒隨時將竹木簡一再削改利用,或移作它用。例如將廢棄的文書簡改作習字簡、廁簡,[24]甚或改削成了某些用途不明器物的形狀(如居延簡393.1)。當然從不少出土簡有火焚的痕跡(如居延簡37.35)可知,應該也有被焚燒,或當作柴薪燃料的。這些都有助於減輕文書保存的壓力。
由此似乎可以推知,為何目前發現的秦漢三國晉代簡牘,除了見於墓葬者,絕大部分是出土於所謂的“井”或垃圾堆中。湖南里耶秦簡、長沙走馬樓漢武帝時代簡、長沙東牌樓東漢簡牘、走馬樓三國時代吳簡和郴州晉簡都在所謂的“井”中發現。一九七三至七四年在甲渠候官遺址出土上萬簡牘,除了F22房址中出土九百餘枚,另有三千餘枚出土於房址外數十公尺的垃圾堆。這些應該都是陸續被拋棄的舊檔案。
2.抄寫、編聯、讀寫姿勢和傢俱
大家都知道秦漢時代經、傳原本分篇抄寫和流傳。即使如《史記》這樣整體性的著作,皇帝要大臣閱讀,也只取一篇(如〈河渠書〉)抄賜。原因很簡單,一套上百篇的大書不論抄寫或存放,都是不小的工程。《史記》有一百三十篇,五十二餘萬字,一篇平均四千字,一簡三十八字計,一篇即有一百零五簡左右。這比永元器物簿的七十七簡還要多出近三十簡,比睡虎地秦簡〈封診式〉部分的九十八支也要多。張家山漢簡出土,整理者根據出土位置,共將五百二十六簡歸入〈二年律令〉的部分。因為原編繩腐朽,也因為這是為陪葬特別抄寫的,其編聯是否完全依照生前使用時的狀態,難以推測。這種陪葬簡冊的一大特點是其不會再真正使用,僅有“貌而不用”的象徵性。因此可以不計使用上是否方便,凡同一標題下的編聯為一冊。如果真供實用,五百二十六簡為一冊,其體積約為永元器物簿的6.83倍,其直徑約為21.56公分。這樣的簡捲不易以單手持握,基本上只能置於几案展讀;限於几案長度,也只能展開一部分,看一部分,再收捲一部分。如此,在閱讀或查找上會造成很多不便。
從這個角度看,我的一個大膽推測是,墓葬中出土的簡冊,凡一冊多達數百簡者,都比較可能是為陪葬而特別抄製的明器,非供實用。以下再以報導較清楚的隨州孔家坡西漢墓出土的日書簡為例。這些簡出土於槨室頭廂。從殘存絹片可知,原來簡冊很可能是包在絹囊內。出土報告說竹簡“大致呈捲狀,基本保持了下葬時的原貌,當係一冊。經清理,共登記竹簡七百餘枚。”又說簡“基本長度為三三.八厘米,寬度○.七至○.八厘米。”[25]如果不計簡冊編聯時,因編繩造成的空隙,七百餘簡編為一冊,此冊最少長達4.9至5.6公尺。此冊單簡長為33.8公分,超過一般23公分的標準長度。姑以居延23公分長竹簡平均重2.616公克計算(參附表二),七百簡可重1,831.2公克。如果據33.8公分的長度換算,一簡重3.84公克,七百簡即達2,688公克。換言之,這份出土日書冊,全長四、五公尺,重達2.6公斤以上。試想這樣的簡冊,捲成一捲,直徑約24.88公分,如果不置於几案,而是單手持握,不論坐或站,邊展邊讀,將是何等不便?
在漢代畫像裡,可以找到單人跪坐,雙手持簡冊,或雙人共持一簡冊,立而觀閱的例子(附圖4~6.1-2),可是從不見有將簡冊置於几案之上而閱讀的。我們固然不能因此否認漢人常常利用几案讀寫簡冊,但必須考慮他們顯然也常常站著或坐著讀寫。如果考慮到書寫和閱讀姿勢以及傢俱的特色,簡冊編聯理論上可以無限延長,為了使用的方便,一般應不會太長吧。
因此,陪葬文書數百簡為一冊的長度並不能反映漢世實用簡冊的長度。從實用角度看,百簡左右編聯為一篇,已可說是合宜長度的極限。我們曾以七十七簡的元永器物簿復製品作持握實驗。一人兩手持簡冊展讀,兩手伸開能握的簡冊長度頂多不過百簡左右(附圖7);再長,即不便完全展開,或必須收捲一部分。永元器物簿冊由七十七枚簡構成,全長九十公分。不論置於几案或手持展讀,都還算方便。迄今在墓葬以外,還不曾出土比它更長的實用簡冊,應該不是偶然。
此外,簡冊編寫先後的問題,也須重新考慮。漢代簡冊是先編再寫或先寫再編聯?學者多認為二者皆有。[26]有人認為“簡冊大多先編聯好後再書寫,特別是長篇書籍”,或者說“通常書籍類的簡冊先編後寫”,“一些籍賬與券書類的簡冊每每先書寫後編冊。”。[27]
先編後書與先書後編誠然都有,例如簡冊上有繪圖於多簡之上的,應屬先編再繪。如果寫字,我以為先寫再編應較為便利,才是常態。[28]就永元器物簿來說,各簡一氣寫下,沒有留下編繩空間,許多字壓在編繩之下,很清楚是先寫再編。[29]像《史記》這樣的長篇著作,依我推想,各篇恐怕也是先寫再編。[30]第一,《史記》各篇長度不一,而且可以相差甚多。短者不及千字(如〈楚元王世家〉、〈司馬穰苴列傳〉、〈循吏列傳〉、〈佞幸列傳〉、〈龜策列傳〉),長者上萬字(〈秦始皇本紀〉、〈晉世家〉、〈楚世家〉、〈趙世家〉),一般自千餘字至八九千字不等,很不一律。[31]如此,在寫一篇之前,不容易預先編好簡冊。第二,如果一篇先預編達百簡,萬一寫錯須削改或須整簡抽換,都會造成不便。當然這不排除先預編若干較短的簡冊;不夠時,將短冊聯綴成長冊。即使如此,仍然不能免去削改時,因冊簡上有二或三道編繩,刀鋒誤傷編繩或礙於編繩,書刀不易使力,或整簡抽換時,須先鬆解再繫緊的諸般不便。
因而不論那類文書,一般恐以先書再編為便。製簡時或先於簡側預刻二或三道編繩契口,書寫臨近契口時,留下編繩的空間,再繼續往下寫。我的同事林素清小姐曾發現居延簡中有在簡體三分之一等長處,分書“上下”字樣,具有標尺作用的簡(例如簡7.26、57.24、273.7,附圖8.1-3),她說:“當簡文須分三欄書寫時,或須以二道編繩編聯成冊時,可利用這樣的標尺置於書寫簡側,對照上、下兩字劃分出的上中下三欄,即可很整齊的寫出三欄文字,而無須於每枚簡上都作欄記。若須於簡上刻畫契口,以利韋編時,利用這種標尺來輔助,也是相當便利的。”[32]標尺簡可幫助書寫者在準確的位置上留下供編繩用的空間。這種標尺簡存在的本身,即可旁證在簡尚未編聯之前,已在簡上書寫。因為如果先行編聯簡冊,寫到編繩左近,越過編繩續寫即可,標尺簡就完全沒有存在的必要。如果簡數多,先寫又不先編聯,也許會造成次序錯亂。不過,避免錯亂並不困難。一則可在簡背編號,一則在書寫時依一定的次序擺放;全篇寫畢,再依次編聯,就沒問題。[33]
當然,這些都不能排除先將簡冊編好,或先編一部分,再寫;不足,再繼續編聯和書寫。過去學者或以簡冊上留有編繩的空間,或以編繩上下二字間距離較一般為大作為證據,來論定某些冊子是先編再書寫。其實留有編繩空間或空間較大並不足以證明編寫的先後。因為不論先書或後書,都一樣可以留下或寬或窄編繩的空間。如果發現編繩上沾有書寫時不慎留下的墨痕,或書寫將近編繩處,字跡出現擁擠、縮小或放大的現象,似乎才是先編後書較好的證據。這樣的證據,尤其前者,似乎較少人注意,也不見報導。
從古人書寫的姿勢看,也以先寫後編較為便利。古人席地而坐,或置簡冊於書案之上。《後漢書•劉玄劉盆子列傳》曾提到書案。更始帝寵姬韓夫人侍飲,見常侍奏事,怒而“扺[扺,擊也]破書案。”書案有可能只供放置文書,未必供伏案抄寫。[34]可是王粲《儒吏論》謂“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于几案之下,長于官曹之閒”云云,似可證刀筆吏的工作和几案分不開。又《鹽鐵論•取下》賢良謂:“東嚮伏几,振筆如[王利器引楊沂孫曰: “如”同“而”]調文者,不知木索之急,箠楚者之痛也。”這應可作為“伏几而書”的明證。如果在几案上書寫,簡冊先編後編皆無不可,不成問題。值得注意的是,在漢代的圖像資料裡,迄今還找不到任何伏案或伏几書寫的例子,反而有圖像,也有文獻可證,漢人常常一手持簡牘,一手執筆,或坐或站,以懸腕懸肘之姿書寫。[35]
例如在河北望都一號漢墓的壁畫裡,畫了許多坐在枰上的功曹和主記之類的地方官吏。他們手中持著牘,所坐的枰旁有硯墨置於地上,卻沒有任何几或案。他們應該都是坐著,兩手分持筆、牘,懸肘書寫。這種情形在望都漢墓榜題為“主簿”的畫像裡看得最清楚。他左手持牘,右手正握著筆(附圖9)。在四川成都青杠坡出土一件畫像磚上,可以看見跪坐的官吏分在主官的兩側,他們手捧簡冊,腰間繫有書刀,身旁也沒有任何書寫時可供憑依的傢俱(附圖10)。換言之,他們如須書寫,很可能也都是坐著,一手持牘,一手執筆。湖南省博物館藏長沙金盆嶺西晉墓出土青瓷俑則非常生動地表現了兩吏對坐,持牘執筆而書的模樣(附圖11)。張朋川和揚之水先生都曾注意到這件材料,並討論了坐姿書寫的問題。[36]
以下再舉一個立姿書寫的例子。二○○○年在秦始皇陵封土西南角K0006號陪葬坑發現八件原有彩繪的文官俑。這八件造型最大的特點是皆為立姿袖手,“腰束革帶,右腰間貼塑出作懸掛狀的削、砥石囊。”左臂與軀幹間有一近橢圓形的3×9公分左右的斜孔,或雙手交合處有一豎向的1.6×4.5公分左右的長方形孔(附圖12.1-3)。[37]發掘報告分析認為懸於腰間的是削刀和磨刀用的砥石,而臂間腋下的橢圓斜孔和雙手間的長方孔原應插有簡牘。[38]這個分析完全正確。發掘者段清波先生說:“八尊袖手立俑恭謹經(站)立,刻畫的是一幅官署中整裝在崗,靜待官署長官到來前的文官群體形像。他們袖手經(站)立,臂夾簡冊,腰掛書刀、砥石,長官一有吩咐,便記錄下來分頭去辦理各種事務。在他們的身上只是缺少兩漢文職官吏必備的毛筆罷了。”[39]這是很生動的描寫。
這裡要強調的是秦始皇陪葬俑已發現數千,各種姿勢或立,或坐,或跪都有,這些所謂的文官俑都以挾牘立姿塑造,應反映了官吏,或者更準確地說,侍從官吏書寫時常見的姿態。可是這批俑畢竟只見持或挾簡牘,沒有擺出書寫的姿態,會令人懷疑真的是站立著書寫嗎?有更積極的證據嗎?在西元五世紀初高句麗德興里古墳的射戲壁畫裡,有人正騎馬馳射,其側站立一人,榜題曰:“射戲注記人”。注記人正一手執筆,一手持牘而書(附圖13.1-2)。[40]這是我耳目所及,站立書寫最明確的例子。此例時代較晚,站立書寫的習慣無疑存在已久。
珥筆的習慣可以旁證書寫常為立姿。前文提到段清波先生發現秦文官俑沒有筆在手。筆在那兒?漢世官員習慣夾筆於耳際。[41]山東沂南北寨漢墓前室西壁畫像清楚刻畫了或站立或跪坐的官吏,手中持牘,耳際插筆。這叫簪筆或珥筆(附圖4.1-2)。《漢書》有“簪筆持牘趨謁”和“持橐簪筆事孝武帝數十年”這樣的話(分見〈武五子傳〉昌邑哀王劉髆條、〈趙充國傳〉)。顏師古注說簪筆是“插筆於首。”筆怎麼插於首?張守節《史記正義》在注解〈滑稽列傳〉西門豹“簪筆磬折”時說得較詳細:“簪筆,謂之毛裝簪頭,長五寸,插在冠前。謂之為筆,言插筆備禮也。”這位唐朝學者認為簪筆的筆,名為筆,其實根本不是筆,而是長五寸,一端帶毛的簪,插在冠前,備禮的飾物而已。他的理解應是混同了漢簪筆之筆與後世師其“遺象”的白筆。白筆一名或始見於曹魏,原指備而未和墨之筆,[42]後來演變為象徵性一端帶毛的簪,插於冠首,或綴於手板頭,甚至又以紫囊裹之,詳見南北朝至唐、宋各朝禮儀或輿服志,不細說。
漢代官員所簪是一枝真正書寫用的筆,不是帶毛之簪。它也不是插於冠前,而是插於耳際,故又稱珥筆。這在前述沂南北寨漢畫裡看得極為清楚。[43]潘安仁為賈謐作贈陸機詩“珥筆華軒”句,李善注引崔駰《奏記》:“竇憲曰:『珥筆持牘,拜謁曹下』。”(《文選》卷二十四,文津出版社,頁1155),曹植也說:“執鞭珥筆,出從華蓋”(《三國志•陳思王植傳》,頁570)簪筆和珥筆在漢世無疑為一事,都是指插或夾實用之筆於耳際。
為什麼要將筆插或夾於耳際?如果是伏几案而書,大可將筆、墨、硯等文具置於几案之上或其旁。揚之水先生即曾指出洛陽朱村東漢墓壁畫,書案上有硯和卮燈。[44]官吏之所以要簪筆於耳,應和他們常常須要站立著侍從長官,或在行動中(從君之後、趨謁、出從華蓋…)站著書寫,沒有其它更方便的地方放置毛筆有密切的關係。[45]久而久之,簪筆於耳,成了習慣,甚至成為禮儀。不但沂南北寨畫像中的官吏在參加喪禮的場合,[46]簪筆在耳,曹魏以後,其變制(白筆)變成官員服飾的一部分。這頗像魏晉以後紙文書雖已普遍,漸不再用笏或牘書寫,官員行禮,卻仍然持笏板在手。
以上所談,無非在於說明漢代因書寫姿勢而形成的一些習慣。如果經常或坐或立,懸腕懸肘而書,則似乎只有使用未編的簡或牘才便於持握。即使持用編聯過的簡冊,也應是不過數簡的短冊;長冊則難於邊持邊書寫。不論是書籍或賬簿類,待完整的一篇抄畢,削改好錯誤,最後再進行編聯,無論如何應是最方便的方式。
後記: 本文得以完成,要特別感謝史語所的林玉雲、楊德禎小姐和楊永寶、丁瑞茂先生、柳立言兄、學棣劉欣寧、游逸飛以及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張德芳和張俊民先生、中國文物研究所胡平生先生的協助。最後另要感謝匿名審查人提供的寶貴意見。2005.12.28/2008.3.18
原刊《古今衡論》17(2007),頁65-101。2008.3.29訂補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1.1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1.2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1.3 1.4
圖1.1-4:128.1簡冊正背面展開(為便於對照,背面照片有意上下顛倒)和捲起的情況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圖2 128.1冊尾編繩打圈結 圖3 掛壁的簡冊 山東臨沂白莊漢墓出土 採自《中國畫像石全集》3,圖11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圖4.1沂南北寨漢墓 官員簪 圖4.2 沂南北寨漢墓 群吏簪筆持牘站立行禮筆跪而雙手持簡冊 孫機 線描圖,《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頁279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圖5.1邢義田藏拓局部,原石藏山東省博物館 圖5.2 局部摹本(邢義田摹)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圖6.1 《中國畫像石全集》3,圖88局部 圖6.2 《中國畫像磚全集》1,圖156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附圖7 2007年劉增貴先生手持永元器物簿復製品,邢義田攝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圖8.1居延簡 7.26紅外照圖8.2居延簡57.24紅外照圖8.3居延簡 273.7紅外照 圖9 望都一號漢墓壁畫 主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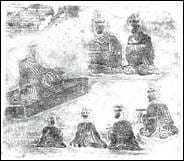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圖10 四川成都青杠坡出土畫像磚 圖11長沙金盆嶺西晉墓出土校書俑湖南省博物館藏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圖12.1 始皇陵K0006坑 文官一號俑 圖12.2 一號俑腰間削刀及砥石 圖12.3 始皇陵K0006坑文官十一號俑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
圖13.1 西元408年 高句麗德興里壁畫古墳,站立持筆的書寫者旁有榜題“射戲注記人”圖13.2 上圖局部
附表一:史語所藏居延木簡重量體積抽樣資料表
居延木簡
簡號
重量(公克)
長(公分)
寬(公分)
厚(公分)
1
3.9
4.69
15
3.2
0.2
2
5.1
2.80
20.8
2
0.3
3
8.1
4.59
7.3
3.6
0.45
4
14.1
7.15
23.8
1.3
1.47
5
21.1
63.91
19.3
5.9
2.23
6
23.2
26.24
24.6
3
1.66
7
26.21
4.86
23.5
2.75
0.15-0.3
8
30.2
2.92
10.9
1.6
0.55
9
30.6
2.69
11.1
1.6
0.5
10
35.5
5.66
22.9
1.1
0.35
11
35.22
5.38
2.8
2
0.38
12
36.8
2.23
22.6
1.2
0.24
13
45.1
41.66
17
3.9
2.33
14
46.17
4.31
9.1
5.1
0.32
15
49.3
5.02
9.8
2.9
0.46
16
57.1
11.38
23.2
3
0.34
17
62.18
3.59
9.5
3.3
0.35
18
81.5
19.39
29.5
1.1-2.2
1.1-2.2
19
82.1
9.2
23.2
2.7
0.4
20
82.18
5.76
10.2
2.7-3
0.5
21
83.3
8.9
8.9
2.6
1.54
22
83.5
15.92
9.3
4
0.34
23
128.1
243.63
24
133.3
10.81
17.6
3.5
0.46
25
133.4
6.65
15.1
2.8
1.1
26
133.5
4.91
16.1
3
0.35
27
133.23
2.72
22.9
1.2
0.31
28
142.12
1.4
9.2
1.6
0.42
29
159.14
6.3
23.5
2
0.38
30
160.15
7.15
23
1.7
0.47
31
179.2
60.63
14.5
7.5
1.87
32
210.35
4.71
23.6
1.3
0.43
33
214.5
3.74
23.2
1.7
0.4
34
229.1+229.2
5.33
30
2.4
0.31
35
236.1
5.02
14.5
1.9
1.38
36
255.21
4.59
7.2
1.1
0.29
37
255.24
6.38
8.5
1.1
0.25
38
258.2+265.12
9.51
15.8
3.3
0.47
39
262.9
2.38
12.3
1
0.4
40
279.11
9.71
15.4
3.4
0.5
41
286.19
21.81
23
4.6
0.75
42
288.19
21.14
12
1.8
0.3
43
293.5
3.67
23.3
1.2
0.29
44
311.3
2.69
23.2
1.2
0.3
45
377.4
33.36
23.1
3.9
1.75
46
393.8
5.14
10.75
1.8
0.5
47
456.5
31.02
48
505.1+505.4
7.53
22.8
1.4
0.53
49
509.13
12.45
23.2
3
0.52
50
513.17+303.15
2.28
23
1.6-1.8
0.2-0.3
51
526.1
96.94
23
6.8
2.46
52
534.3
3.07
23.7
0.9
0.32
53
562.1
21.81
23.2
6
0.49
54
562.13
8.82
22.9
2.2
0.58
附表二:史語所藏居延竹簡重量體積抽樣資料表
居延竹簡
簡號
重量(公克)
長(公分)
寬(公分)
厚(公分)
1
13.9
1.72
22.4
0.7
0.13
2
15.1
5.03
23.6
1.2
0.42
3
25.1
2.64
22.8
1
0.26
4
34.23
1.77
23.1
0.9
0.22
5
35.7
3.13
23.2
0.8
0.2
6
35.18
2.97
23
0.9
0.16
7
35.23
2.79
22.8
0.6
0.2
8
37.37
3.22
23.3
0.8
0.28
9
57.6
2.69
25.8
1
0.2
10
142.27
1.69
23
0.8
0.12
11
313.32
1.59
23.1
0.7
0.18
12
501.1
2.15
22.7
0.7
0.17
平均
2.616
23.233
0.841
0.211
13
524.5
0.95
11.5
0.7
0.17
14
539.2
0.96
11.3
1.2
0.42
平均
0.955
11.4
0.95
0.295
附表三:單行簡重量體積資料表
單行一尺木簡
簡號
重量(公克)
長(公分)
寬(公分)
厚(公分)
備註
1
35.5
5.66
22.9
1.1
0.35
2
36.8
2.23
22.6
1.2
0.24
3
133.23
2.72
22.9
1.2
0.31
4
210.35
4.71
23.6
1.3
0.43
5
293.5
3.67
23.3
1.2
0.29
6
311.3
2.69
23.2
1.2
0.3
7
505.1+505.4
7.53
22.8
1.4
0.53
8
534.3
3.07
23.7
0.9
0.32
平均
4.035 23.125
1.188
0.346
9
57.1
11.38
23.2
1
0.34
三簡加編繩
附表四:紅柳、胡楊、松木、竹標本重量體積表 2006.10.12-13
長(公分)
寬(公分)
厚(公分)
重量(公克)
紅柳1
23.13
1.18
0.34
6.48
紅柳2
以下略同
以下略同
以下略同
7.75
紅柳3
7.81
紅柳4
7.30
平均
7.335
松木1
4.07
松木2
3,68
松木3
標本不夠完整,未列入計算
平均
3.875
胡楊1
3.84
胡楊2
4.19
胡楊3
3.15
胡楊4
3.14
胡楊5
3.37
平均
3.538
台灣竹1
4.24
台灣竹2
4.76
台灣竹3
3.63
平均
4.21
附錄: “永元器物簿”的簡數和編號問題
長期以來自查科爾帖(A27, Tsakhortei)出土迄今最完整的漢代簡冊存在著簡數和編號說法不同的問題。因為我們有機會檢查原簡冊,應該作一次澄清。
一九五六年索馬斯特勒姆編輯出版的《內蒙古額濟納河流域考古報告》只非常簡略地提到這一完整的簡冊七十八枚出土於查科爾帖(A27)烽燧遺址建築的乙室(Room B)。[47]貝格曼的考古日記裡則曾稍詳細提到,一九三○年十月廿九日是靳士貴發現了這一簡冊,並說這一冊子是“由七十八枚有字木簡組成”。[48]有些文獻據之以為永元器物簿由七十八枚簡組成,[49]但最早作考證的勞榦先生認為此冊由七十七枚簡組成。[50]這件獨一無二,迄今最長的簡冊,到底由幾枚簡組成呢?須要澄清。
這七十八枚簡據貝格曼日記描述“捆在一起”的狀態,出土時應該是捲在一起的。[51]因為編繩仍在,又未細究內容,很容易就將七十八枚簡視為同一個冊子。在整理的過程裡,不論是最早的釋文或反體照片,都將“入南書二封”云云沒有編繩相連的一簡置於全簡冊之前。例如一九四三年勞榦先生在四川李莊出版石印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就是如此。此書完全沒有收錄簡影,唯一例外是卷三,勞先生特別為此簡冊作了起首部分的摹本。這個摹本很清楚將“入南書二封”一枚置於最前,沒有編繩,其餘則編繩相連。不過,勞先生顯然已查覺到“入南書二封”一簡和其它七十七簡的編冊無關。
這批萬餘枚的漢簡是運到北平進行整理時,才加上了編號。編號是依據和出土地點緊密相關的採集品包號,同一地所採集的往往編有好幾個號碼。查科爾帖(A27)烽燧遺址乙室共出土簡九十枚左右,即編有92、128、130、151、251、552不同的號。編號時,有些是以朱砂將編號寫在簡的背面或側面,有些是寫在橢圓形的小紙吊牌上,再將吊牌以細繩繫在簡上。我們曾反覆檢查簡冊正背面,確實沒有發現任何編號痕跡,也不見橢圓吊牌。
現在所能見到最原始用來製版出書用的反體照片上,此冊旁邊沒有編號。一九四三年石印的《居延漢簡考釋-釋文之部》,一九五七年在台北出版《居延漢簡-圖版之部》和一九六○年出版的《居延漢簡-考釋之部》也都沒有編號。台北版《居延漢簡-考釋之部》是據圖版順序排列,在圖版570-575各頁的釋文,也就是永元器物簿的釋文之前,甚至都明確注明“未編號”(《居延漢簡-考釋之部》,頁190-192)。
勞書各簡都有編號,唯此七十八簡沒有。那麼,此冊編號128.1和“入南書二封”一枚編為128.2號是怎麼來的呢?在出版的資料中,最早注明這七十八簡編號為128.1和128.2的是一九五九年科學出版社出版的《居延漢簡甲編》。《甲編》圖版和釋文曾另行編號,並將此七十八簡編為第一號。但書後所附〈本編簡冊索引〉卻在第一號之原簡編號欄下注記:“128.1, 128.2 (勞書未編號)”,給了兩個原簡編號。128.1是指七十七枚簡組成的永元器物簿或勞先生所說的廣地南部兵物冊,128.2是那枚沒有編繩的“入南書二封…”一簡。從此《居延漢簡甲乙編》和《居延漢簡釋文合校》都沿用了這樣的編號。
《甲編》編號又是據何而來?現在終於可以較肯定地說,在北平作釋文時永元器物簿即有了128.1的編號。今年十一月廿六至廿九日,我到香港大學圖書館看到了一九四○年留在港大馮平山圖書館,未隨居延木簡送到美國,由馬衡、向達、余遜、勞榦等最初作釋文時的種種記錄。[52]在圖書館整理這些記錄時,一個名為“校閱漢簡記錄”的黃色牛皮紙袋內,有一件一眼可以認出是勞榦先生手書,題為“送往上海印影木簡及送往南京美展陳列品細目”的冊子,在展品目錄下共三件:第一件即編號為128.1的七十七枚簡組成的永元器物簿冊。目錄是這樣記錄的:
包號 包 內 件 號
1281 2
(1字下有朱筆注:冊,計簡七十七片編成)
另一件是三簡編連在一起的57.1,第三件展品是居延筆模型。由此可以清楚知道永元器物簿不是沒有編號,而且早已編成128.1和128.2。由於找到這件早期記錄,永元器物簿的編號和件數問題應該可以定案了。
2007.11.30自港返台後定稿
(編者按:[1]另一個相關的故事是秦始皇“衡石量書,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史記・秦始皇本紀》)。〈集解〉以為石為“百二十斤”,瀧川龜太郎以為非指確數,“但言有定程耳。”(《史記會注考證》卷六,頁57)。
[2]冨谷至曾從“書籍”和“賬簿”兩大類不同性質的簡冊來考慮簡冊的收捲方式,他也以128.1簡冊為例,證明該冊性質為賬簿,收捲應是簡冊起首收在內,末尾在外。參冨谷至著,《秦漢刑罰制度の研究》(東京:同朋舍,1998),頁9;中譯參柴生芳、朱恒曄譯,《秦漢刑罰制度研究》(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6),頁4-5;又見冨谷至,《木簡・竹簡の語る中國古代》(東京:岩波書店,2003),頁72-79;劉恒武中譯本,《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頁45-48。揚之水先生論證雖小異,但基本分類意見和冨谷一致,參氏著,《古詩文名物新證》(二)(北京:紫禁城出版社,2004),頁369。
[3]冨谷至在討論竹木簡的製作時,也已注意到製作成批標準型簡和製作書冊時,竹比木更合適。參冨谷至,《木簡・竹簡の語る中國古代》,頁98;劉恒武中譯本,《木簡竹簡述說的古代中國》,頁60。
[4]參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南寧: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96-98。
[5]錢存訓指出漢代用簡以竹為常, 木簡多用於不產竹之地。參錢存訓,《中國古代書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1975),頁85。冨谷至也有類似見解,他認為除西北地區外,漢代一般編綴式的簿籍和書籍一般用竹,各種證明文件、檢、檄、楬、符等才使用單支的木牘。參冨谷至,《木簡・竹簡の語る中國古代》,頁95-100。不過近年刊佈的湖南龍山里耶秦簡三萬七千餘枚,除極少數竹質,幾全為杉木質木簡或木牘。龍山里耶一帶不能說不產竹。雲夢睡虎地秦律〈司空律〉中有一條說:“令縣及都官取柳及木柔可用書者,之以書;無方者乃用版。”可見秦代縣一級以及都官公文書用木方或木版。里耶在秦代為遷陵縣城,其所出簡牘當為縣之文書,正可證實秦律的規定。不過,這應是指正式的公文書而言,不排除副本或其它用途的文書用竹。一九九六年公佈的長安未央宮遺址出土西漢王莽時期的簡,由杉木製成,內容多關祥瑞,原應編聯為冊;不久前公佈的南越國宮署簡,內容上明顯屬簿籍類,簡也是木質。又《鹽鐵論・論功》文學論匈奴“略於文而敏於事”時,說匈奴“雖無禮義之書,刻骨卷木,百官有以相記,而君臣上下有以相使。”(王利器校注本,頁326)漢初中行說曾入匈奴,教“單于左右以疏記,以計課其人眾畜物”(《史記・匈奴傳》,頁2899)。所謂刻骨,疑因匈奴多牛羊,利用其骨刻書,或如近年未央宮側遺址所出骨簽之類;卷木則無疑是木製編聯之卷冊,這當是仿西漢簡冊之制而來。因此簡用竹或木,似難一概而定,錢、冨谷說猶待更多資料驗證。參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北京:文物出版社,1978),頁83;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長沙:岳麓書社,2006),頁179;社科院考古所,《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北京: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1996),頁238;廣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廣州市南越國宮署遺址西漢木簡發掘簡報〉《考古》3(2006),頁3-13。
[6]關於定期銷毀之制可參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桂林:廣西教育出版社,1999),頁227-232。
[7]參邢義田,〈從“如故事”和“便宜從事”看漢代行政中的經常與權變〉《秦漢史論稿》(台北:東大圖書公司,1987),頁352-353。
[8]近年長安桂宮遺址出土王莽封禪玉牒。此玉牒之所以藏於桂宮,馮時曾細加討論。可參馮時,〈新莽封禪玉牒研究〉《考古學報》1(2006),頁31-58。另青海海晏縣曾出土王莽虎符石匱,李零曾詳考金匱石室之制。參李零,〈說匱〉、〈王莽虎符石匱調查記〉《入山與出塞》(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頁351-357。
[9]社科院考古所,《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頁17-18。
[10]王國維原著,胡平生、馬月華校注,《簡牘檢署考校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頁 92-96。
[11]可參王金玉,《宋代檔案管理研究》(北京:中國檔案出版社,1997),頁47;周雪恒主編,《中國檔案事業史》(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4),頁209-217。承柳立言兄示知並借閱二書,謹謝。
[12]相關討論可參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頁204-232。
[13]《漢長安城未央宮1980-1989年考古發掘報告》頁91說:“遺址中的骨簽大多出土于F2、F3、F4、F5、F6、F9、F10、F11、F12、F13、F14和F15中(包括其附近),主要分布于上述房屋牆壁附近,推測這些骨簽原來於置于靠牆壁而立的架子上。”同書頁238說:“在前殿A區遺址第3層(漢代文化層)發現了被火燒的木簡,它們分別出于F13和F26之內。F13的木簡尚未寫字,F26出的木簡墨書棣字。”對骨簽出土的狀態可惜沒有更進一步仔細的報導。
[14]簡冊照片參李均明,《古代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頁142,圖15。
[15]參魏堅主編,《額濟納漢簡》(桂林: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頁73。
[16]參胡平生,〈“扁書”、“大扁書”考〉,收入中國文物研究所、甘肅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敦煌懸泉月令詔條》(北京:中華書局,2001),頁48-54;馬怡,〈扁書試探〉《簡帛》第一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頁415-428。馬怡先生已指出“專部士吏典趣輒”冊兩頭編繩有環,可以懸掛。
[17]此畫像中編繩較一般麻繩為粗,疑為韋編之皮韋,唯無確證,俟考。
[18]陳夢家,〈由實物所見漢代簡冊制度〉《漢簡綴述》(北京:中華書局,1980),頁295;蕭靜華,〈從實物所見三國吳簡的製作方法〉《長沙三國吳簡暨百年來簡帛發現與研究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北京:中華書局,2005),頁26。感謝胡平生先生提示資料。
[19]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睡虎地秦墓竹簡》,頁109。
[20]《論衡•謝短篇》:“牆壁書畫厭火丈夫,何見?”《風俗通義》佚文:“殿堂宮室,象東井形,刻作荷菱。荷菱,水物也,所以厭火。”(《藝文類聚》卷六十二、六十三)河南、陜西漢墓出土有“東井滅火”榜題之陶井模型或畫像磚甚多,不一一細舉。
[21]汪桂海,《漢代官文書制度》,頁227-232。
[22]參《唐律疏議》卷十九,頁351;仁井田陞著,栗勁譯,《唐令拾遺》(長春:長春出版社,1989),頁534。
[23]參王金玉,《宋代檔案管理研究》,頁38。
[24]胡平生,〈敦煌馬圈灣簡中關於西域史料的辨證〉附錄二:“馬圈灣木簡與‘廁簡’”,收入吳榮曾主編,《盡心集-張政烺先生八十慶壽論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96),頁296-297。
[25]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隨州市考古隊編,《隨州孔家坡漢墓簡牘》(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29-30
[26]例如李均明、劉軍,《簡牘文書學》,頁15;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 (北京:中華書局,2004),頁123;胡平生,《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武漢:湖北教育出版社,2004),頁19;駢宇騫、段書安,《二十世紀出土簡帛綜述》(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68;冨谷至,《木簡・竹簡の語る中國古代》,頁72-79,劉恒武中譯本,頁45-48。
[27]張顯成,《簡帛文獻學通論》,頁123;胡平生,《長江流域出土簡牘與研究》,頁19。
[28]近年新出土湖南龍山里耶秦簡三萬七千餘枚,基本上是地方政府的文書檔案,出土報告說這些木簡或木牘有“兩道編繩或無編繩,編繩係書寫後再編聯,尚未見到先編聯後書寫的。”見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里耶發掘報告》,頁179。
[29]令人較納悶的是如果是先寫後編,為何此冊第三和第四段編繩所編的最末一簡會是空簡?仍然沒有好的解釋。就內容和編繩言,此冊前三部分各有十六簡,最後一部分為廿九簡,共七十七簡。
[30]近日讀到陳劍先生文,指出李天虹和馮勝君都曾論證郭店楚簡絕大部分篇章都是先寫後編,可以參照。參陳劍,〈郭店簡《尊德義》和《成之聞之》的簡背數字與其簡序關係的考察〉《簡帛》第二輯(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頁219及注1。
[31]感謝學棣游逸飛代為統計《史記》各篇白文字數。最短的如〈司馬穰苴列傳〉、〈楚元王世家〉各有七百餘字,最長如〈晉世家〉、〈秦始皇本紀〉各有一萬二、三千字。年表字數難以計算,不列入。
[32]林素清,〈《居延漢簡補編》識小二則〉《居延漢簡補編》(台北: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98),頁57-60。
[33]簡背編號已在戰國楚簡上發現,基本上和簡序有關。陳劍指出“最有可能的,應該是在有關竹簡已經抄寫好之後,出於某種目的從後往前清點數目,並隨手將竹簡提起倒過來翻面後記下的數目字。而且,這個清點記數的過程最可能在還未編成冊的散簡狀態下進行的。”這是陳劍觀察郭店簡《尊德義》和《成之聞之》的簡背數字得到的結論,雖然仍有數字和簡序不合的情形,未能得到妥善解釋。陳先生所說應是數字編碼的一種方式,應還有其它方式,暫不細說。請參注29引陳劍文,頁209-225。
[34]孫機和揚之水談几案,只談到案有食案和書案等,書案供放置文書,沒說是否也在案上書寫。參孫機,《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北京:文物出版社,1991),頁216-219;揚之水,《古詩文名物新證》(二),頁377-383。
[35]《莊子•田子方》:“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這裡說的雖是畫圖,但站立著書寫應也是常事。《韓詩外傳》卷七謂:“趙簡子有臣曰周舍,立於門下,三日三夜。簡子使人問之…對曰:願為諤諤之臣,墨筆操牘,從君之後,司君之過而書之。”周舍持筆墨牘,願隨簡子之後司其過而記之,想來也應是隨行隨記,站立著書寫吧。
[36]張朋川,〈中國古代書寫姿勢演變略考〉,《文物》3(2002),頁85-86;揚之水,《古詩文名物新證》(二),頁386-387。
[37]秦始皇陵考古隊,〈秦始皇陵園K0006陪葬坑第一次發掘簡報〉,《文物》3(2002),頁4-31;陜西省考古研究所、秦始皇兵馬俑博物館編,《秦始皇帝陵園考古報告2000》(北京:文物出版社,2006),頁73-85。
[38]秦始皇陵考古隊,〈秦始皇陵園K0006陪葬坑第一次發掘簡報〉,頁29;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園K0006陪葬坑性質芻議〉《中國歷史文物》2(2002),頁59-66;《秦始皇帝陵園考古報告2000》,頁260-262。
[39]段清波,〈秦始皇帝陵園K0006陪葬坑性質芻議〉,頁63。
[40]高句麗文化展實行委員會編,《高句麗文化展》(東京:高句麗文化展實行委員會,出版年不明,疑在1985年左右),頁38。
[41]站立書寫時,如何用筆沾墨,至今還不了解。疑秦漢之時除塊條或丸狀之墨,還有其它形式。前引《莊子•田子方》:“宋元君將畫圖,眾史皆至,受揖而立,舐筆和墨…”郭慶藩《莊子集釋》點校本校記中引陸德明《經典釋文》云舐:“原作□,字當作□。《說文》作□,云:以舌取食也。”由此可知,或以筆入口取津液以和墨。
[42]《太平御覽》卷六八八“白筆”條引《魏略》曰:“明帝時嘗大會殿中,御史簪白筆,側階而坐。上問左右:此何官?侍中辛毗對曰:此謂御史。舊簪筆以奏不法,今但備官耳。”辛毗之意是曹魏時,殿上御史已不再奏不法,筆簪而不用,不濡墨矣。同條引徐廣《車服雜注》曰:“古者貴賤皆執笏,有事則書之,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台灣商務印書館景印本,1997,頁3201)
[43]《晉書•輿服志》:“笏者,有事則書之,故常簪筆,今之白筆是其遺象。”孫機在討論有幘之冠時,借用沂南北寨漢墓畫像中的戴冠人像,並標示其耳側之筆為白筆(見前引《漢代物質文化資料圖說》,頁231,圖版57;《中國古輿服論叢》增訂本(北京:文物出版社,2001),頁164附圖),似嫌稍有不妥。如果承認沂南墓為漢墓,則畫像中的筆是真筆,而不是漢以後得其遺象的白筆。也有人認為沂南墓晚於漢,則又當別論。
[44]揚之水,《古詩文名物新證》(二),頁376,圖20-20:1-2。
[45]還有一個不好理解之處,如果站立書寫,墨置於何處?如何以筆沾墨?我懷疑古人書寫或以筆沾墨汁,或沾有某種黏合劑的鉛粉或用鉛條。《西京雜記》卷三提到楊子雲好事,“常懷鉛提槧,從諸計吏,訪殊方絕域四方之語。”胡平生和馬月華理解懷鉛為“常常懷裡揣著鉛粉筆”(《簡牘檢署考校注》,頁51注4)。這是一種理解。另一可能是鉛條。《西京雜記》僅說“懷鉛”,此鉛可證供書寫用,唯不知其形。如為鉛條狀之筆,即無沾墨問題,便於行動中或站立時書寫。中國自殷商即已掌握了鉛的使用,先秦鉛器出土甚多,參李敏生,〈先秦用鉛的歷史概況〉《文物》10(1984),頁84-89。漢墓出土有買地鉛券、代役鉛人、鉛錢,可見用鉛並不少見。唯迄今似不見有書寫用的鉛條出土。姑言之,俟考。
[46]揚之水先生認為此圖為上計,但沒有解釋為何在上計的場合會出現繫於樹下或由人牽繫的羊、置於案上整治過的禽獸、酒罈和外有封檢,不知內盛何物的囊袋、篋笥。上計時,固有計篋和書囊,但如揚文所附馬王堆一號漢墓出土的方形竹笥外也有封檢。單從外觀無以得知其內是否為計簿或其它。私意以為沂南漢墓前室東西南三壁上的這些物品比較不像上計吏所攜的“計偕物”。所謂計偕物應包括具有地方特殊性的“方物”(如揚文頁478所引應劭所貢伏苓、紫芝、鹿茸、五味等藥物),不會是極普通的羊或禽兔之類。圖中所示羊酒等比較像是參加祭禮的人帶來的祭品或助祭的食物。因此,我認為這是喪祭圖較合宜。參揚之水,〈沂南畫像石墓所見漢故事〉《古詩文名物新證》(二),頁470-478。
[47]Bo Sommarström, Archaeological Researches in the Edsen-gol Region Inner Mongolia(Stockholm, 1956), p.294及圖版XIX文字說明。
[48]貝格曼著,張鳴譯,《考古探險手記》(Travels and Archaeological Field Work in Mongolia and Sinkiang-A Diary of the Years 1927-1934)(烏魯木齊:新疆人民出版社,2000),頁151。
[49]如《居延漢簡甲乙編》(北京:中華書局,1980),下冊,頁311。
[50]勞先生在最早出版的石印本《居延漢簡考釋-考證之部》(李莊: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1944)卷一,頁74下即指出廣地南部兵物冊為七十七簡。
[51]貝格曼著,張鳴譯,《考古探險手記》,頁151。
[52]關於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館藏編號:特796.7 10),目前僅有該館人員張慕貞小姐所寫報導。詳見港大圖書館出版的《焦點新聞信》(Focu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Libraries newsletter)new series Vol.5, No.4, June 2006. 或上港大圖書館網站: http://lib.hku.hk/general/focus2007.11.30.又我已寫成〈香港大學馮平山圖書館特藏部藏居延漢簡整理文件調查記〉。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549.html
以上是关于中国古代史-漢代簡牘的體積、重量和使用—以中研院史語所藏居延漢簡為例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