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初政府的设立和制度的建立为之后的府院之争埋下了祸根。民国法律确立了所谓的内阁制度,但这一制度在民初的中国由于水土不服发生了变异,以至于演变成为民国初年的府院之争。那么,民初的府院之争究竟是如何演变的?府院之争的产生有哪些方面的原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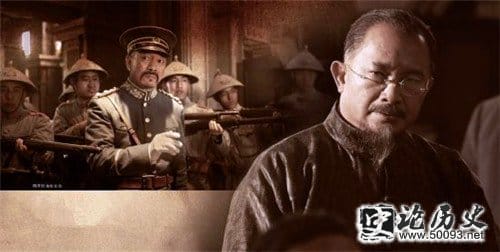
(一)袁世凯总统时期的府院之争
袁世凯当上临时大总统、组成唐绍仪内阁不久,即发生府院冲突。袁氏主总统制,唐氏主内阁制,观念不同,自然会产生摩擦。“唐氏自任国务总理,颇有意举责任内阁之实,以避袁氏与各方之冲突,而袁之不谅,且疑唐挟国民党以自重,有独树一帜之意”,以至府院两处意见不合,各走极端,总统府对“发一议,出一令,必经国务院之阶级,且有时驳还,深病之”,总理甚至在总统府与袁面争不屈,以致于总统府的侍从武官都认为总理经常“欺侮”总统,于是,府院之间形成对立。双方最终因为王芝祥督直问题直接导致二人间关系的破裂,致使唐绍仪提出辞呈,蔡元培、王宠惠、熊希龄、宋教仁、王正廷等阁员继之,以致第一届责任内阁迫于强权政治而解体。袁、唐府院之争,表面上是权力之争,但实际上是政体之争。
此后因袁世凯占据绝对优势,其他继任总理只好顺从,“总理遂一任袁之指挥”,府院之间相安无事,以致内阁制精神完全被漠视,府院关系完全颠倒,民初内阁“并非由参议院产生,也不是由多数党领袖组织,而是完全由袁世凯个人定夺。从西方移植过来的政党内阁制也完全变了种,不论叫‘总统内阁’也好,还是叫‘内阁政党’也好,实际上都不过是袁世凯的秘书院”,几乎成袁家天下。
(二)黎元洪总统时期的府院之争
袁氏既殁,成为北洋领袖的段祺瑞以国务院的名义宣布依据《中华民国临时约法》第29条以副总统黎元洪“代行”中华民国大总统,府院关系则呈现出另一种局面。
此时,控制北京政权的并非黎元洪,而是担任总理的北洋中坚段祺瑞。以段祺瑞为代表的北洋系对于总统落入非北洋的黎元洪手中,非常不满。而不甘心做傀儡和签字机器的黎元洪,意图以恢复国会,乘机扩张,以图有一番抱负。而作为内阁总
理兼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利用《临时约法》规定的内阁制把持权力,不让其参与政事,把黎元洪排除于政局之外,以架空、挤走非北洋系总统为目标,导致府院之间出现这样的对立局面:“国务院议事前既无议事日程,事后又无议事记录,总理不见总统,但凭院秘书长往来其间。发一令总统不知用意,用一官总统不知来历……总统偶有所询,院秘书长则以事经阁议,由内阁负责为答,大总统无见无闻,日以坐待用印”,以至于府院双方渐生暗潮,矛盾和冲突不断,并不断升级,最终因对德外交问题而爆发政坛上的大震荡。这就是学界多有述及的“府院之争”。
事情起源于1917年1月德国宣布施行“无限制潜艇战”,美国宣布对德绝交,准备参战,并要求中国与其采取一致行动。日本获悉后,唯恐落在美国后面,也积极支持中国参战。美国为了与日本抗衡,随即改变态度,反对中国参战。而此时中国政府在对德绝交与宣战问题上分为两派:以段总理为首的赞成派和以黎总统为首的中立派。此时的外交问题,实为府院关系问题,“府方谋倒段、院方谋倒黎”,于是双方均离开正文而别寻途径。3月4日,段祺瑞偕阁员到公府谒见黎元洪,请求在对德绝交案上盖印,黎总统以“对德绝交”须国会同意为由,未允盖印。段祺瑞即以“内阁政见与元首不合,则内阁去职为世界立宪国政治之原则”,愤愤岀府,辞职赴津。黎本想批准段的辞呈,但督军团拥段通电吓得黎改变了初衷,同意“绝交咨文,可照盖印”,并浼张国淦及副总统冯国璋赴津斡旋,并承诺不干预内阁的三条件。在此情况下段总理于6日回京照常视事。3月8日,绝交咨文盖印,10日、11日,众参两院分别通过此案。14日,黎总统公布此项文告,宣布与德国断绝外交关系,绝交风潮平息。但段意尤未足,为得到列强的援助,强化北洋势力,欲进一步对德宣战。而为了遏制甚至消灭北洋势力,黎派诸人暗中勾结了一部分国会议员,极力破坏参战案,以至于参战案竟演变成为军人与国会议员之争。5月6日,国务院通过对德参战案,并迫使总统盖印。5月10日,国会开会审议此案时,傅良佐的“公民团”事件使议会与内阁的关系至为紧张,国会遂决定无限期搁置,并要求黎元洪罢免段祺瑞总理职。面对如此严重的问题,黎元洪从国会之请,以美国公使“为后盾”,于23日免去段的本职,以外长伍廷芳代理,另提李经羲为国务总理。免职令下,段即卸职赴津,发布通电,否认免职令的效力,扬言另组临时政府、武装倒黎,府院之争白热化。当参战案搁置之际,督军团召开徐州会议,讨论时局解决办法,决定向黎氏提出解散国会、改正宪法、健全内阁、屏斥佥任四条件,于必要时得进行复辟,以威胁黎元洪。各督军亦纷纷宣布与中央政府脱离关系。黎元洪益感孤立,遂电招张勋入京调停,并以步兵统领江朝宗代理国务总理副署解散国会的命令,于6月12日解散国会。6月14日张勋入京,7月1日,复辟乱出,7月2日,黎元洪电南京冯国璋代行总统职权,复命段祺瑞为国务总理,并避走日本使馆。段看到驱逐黎元洪和解散国会的目的已达到,于7月4日马厂“誓师”,三造共和,17日,组织新阁,重新控制北京政府。黎、段府院之争以此了结。
(三)冯国璋总统时期的府院之争
至冯国璋和段祺瑞分别占据了总统府与国务院,府院均归北洋掌管,“似为北洋当阳之日,应该可以天下太平了”。然而,北洋中的冯、段,因为和战问题潜滋着直皖两系的暗斗,北京政府成为双方争斗目标,而其斗争又以军队为后盾,以至于此时的府院之争呈现另一种局面。
三造共和后,段派对总统人选问题发生分歧,一派认为不要让副总统北来,就由总理摄护,另一派主张由冯国璋北上代理,而张国淦则主张仍请黎出来。但最后段祺瑞主张由冯国璋北来。冯因听到有人主张由段代行总统,故不愿意北来就职,于此埋下了冯、段矛盾的种子。此时,汤化龙代表旧国会请冯国璋到京代行总统职,段援引研究系组成联合内阁,段阁再度成立。8月1日,冯代总统入京就职,数月来的对德宣战案,14日经国务会议全体阁员署名,总统盖印公布。而此时对外问题乃转变而为对内问题,表面上南北统一问题,亦可曰和战问题。对此冯主联合,段主用兵,二者意见素不相容,“冯为总统,段仍为总理,益思凭借权位,以扩张个人势力,而府院问题又起矣”。但此时之府院之争已不同以往。“从前黎、段时期,段握有实力,黎不过政客而已,尚是以虚击实;冯、段既各具相当力量,则是以实碰实”。冯自认为与段为数十年心腹之交,今后再也不会有府院之争了,就是在一般人心里,以为冯、段本为同学,时局结症所在,无不可以推诚披臆,互相谅解,不但以前府院之争不致重演,而大局之解决,亦颇有希望。可段自居责任内阁,把总统看做一个“活动的盖印机器。”而冯国璋也是个有军队、有地盘、有势力、有野心的实权人物,不想甘当“活动的盖印机器”。于是各自代表直、皖两系,公然对峙,再次形成府院之争。
此次府院之争的焦点,乃以何种方式统一全国,实质是为各自的利益而战。皖系主张武力统一,而直系主张和平统一。冯、段真正冲突首先发生在湖南战事问题上。1917年10月,段祺瑞派直系军队进入湖南,与南方护法军作战,希望削弱南方与直系势力。可到了11月14日,前线直系军队宣布停战议和,直隶、江苏、湖北、江西等省督军发表联合通电,主张与军政府和平解决。在武力统一受挫的情势下,段于20日提出辞职,冯毫不客气地于11月22日下令准免,段阁瓦解。段免职后仍以参战督办的名义掌握皖系军队,依然握有压迫内阁、操纵内阁的大权,被称为“太上政府”。12月2日,段策划北方十督在天津举行督军团会议,迫使冯国璋于12月16日重新下令讨伐西南。此时,西南军阀陆荣廷提出恢复国会、停止湘粤进兵和拥护冯国璋继任总统,作为取消两广独立的条件。冯发出停战布告,责成南北两军停止敌对行动。12月31日,北方十督发表通电,坚决反对恢复旧国会,主张以皖系控制的临时参议会代行国会职权,选举正式大总统,企图“合法倒冯”。正当主战派挥兵南下之际,又发生奉军入关“兵谏”,皖奉联合,冯国璋被迫改组内阁。1918年3月17日,内阁总理王士珍发出“阳电”,向督军团辞去内阁总理职。同日,督军团又在天津开会,决定要求恢复段内阁。冯氏无可奈何,屈服于段派,于3月23日下令署国务院总理王士珍免职,特任段祺瑞为国务总理。
段祺瑞第三次组阁后,继续推行他的武力统一政策及原定“合法驱冯”的计划,1918年8月12日,皖系操办的安福国会开幕,1918年9月4日,冯国璋自知无力抵抗,提出以段祺瑞同时下台为他下野的条件,段祺瑞也表示与冯同时下野。安福国会依段意将徐世昌抬出来,既可以解决冯、段之争,又有解决南北战争的希望,选举徐世昌为总统。10月10日,徐世昌就任大总统,冯、段同时下野。冯、段的结局,形式相似,内容则完全不同。段祺瑞不过是以退为进,他依旧在幕后(通过安福系)控制着中国政治,取得了彻底胜利,而冯国璋则为彻底的失败者。
继冯国璋之后,又有徐世昌、黎元洪相继为总统,此二人在任期间,均为傀儡,完全听从于军阀操控的内阁而无所作为,府院之间也曾经因为秘密费和制宪费而发生过争议,分别迫使徐、黎告别政坛。贿选总统曹锟任总统期间,府院之间没有什么摩擦,故不赘述。
二、民初府院之争原因分析
从府院关系演变的几个阶段来看,府院关系常常表现为“府院之争”,“虚位”的总统常常与内阁发生冲突。府院之争几乎伴随着整个民国初期的政治运行过程。
从上面的叙述可看出,民初府院之争有三种形式:第一、强势的总统和弱势的总理之间的冲突;第二、弱势的总统和强势的总理之间的冲突;第三、实力相当的总统和总理之间的冲突。府院之争的结果则取决于总统和内阁各自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消长。袁世凯时期,由于袁世凯的过于强势,内阁完全被压服于总统的威权之下,而袁之后,总统是以虚击实,往往被玩弄于内阁强人的股掌之间。而当二者实力相当时,则以实碰实,依战争来决定胜负属于哪一边。“府院之争”的胜负不管属于谁,都标志着宪法并非权力冲突的最高规则,其后的实力特别是武力则是民初政局维持的另外一种规则,反映出内阁制度在民初的异化。
现在的问题是,为何会持续发生“府院之争”?从表面上看,“府院之争”是两个国家机构之间为争权而发生的矛盾冲突,是任何一个民主法制国家都不可避免的,不论从国家权力结构的角度或者是从利益集团关系的角度来说,都显得是一种必然的状态。但是发生在刚刚脱离有几千年专制传统的、初建共和的民国,则不能不有其特殊原因。
首先是传统的帝王权力观、皇权思想的体现。
谷钟秀分析说:“内阁制度,国务员对国会负责任,故国务员组织之国务院,当然为政治之总枢。总统无论有何种意思之表示,不经国务员之副署,不生效力,总统不能侵越国务员之权限。然,中国承数千年专制惯习一般心理上之感想,是总统府之于国务员亦犹前清之皇上与军机大臣。且以雄才大略之总统,又岂能受法律上之束缚而自甘无为?于是国务员与总统府权限问题,当唐内阁初成,已惴忧,无以解决”,“未几,拒绝副署之事实果现,终以不顾副署,而总统之命令仍为有效。”王之祥督直案即是一例,“此例一开,内阁制度,根本上已失所凭依,国务员将永为无意识之负责任”。对于府院关系,吴佩孚曾于1918年给段总理的一封电报说出了当时的人们对府院关系的认识:“责任内阁系巩固国家之中枢,政令所由出。查民国约法,宣战媾和许大总统以特权,未闻以此种特权许内阁也。况内阁即昔日之宰辅。宰辅者,世运之隆替,国统之枢纽也。曰内阁,曰丞相,名殊意一。其责任,宰辅朝野上下之权衡,以辅左右出入之政也……掌天下安危、操邦国存亡,实责任在宰辅一人。元首不仁,则可驱为汤武,元首而仁,则可希乎尧舜。是世无不仁乱政之元首,而有不仁危国之宰辅也。……殊不知宰辅总百官之政,元首之口舌也。一旦喉关固闭,言路弗通,则国情无所达。”这段话似乎在指责内阁,而同情元首,是一种传统的思维观念,实为不明内阁制之精义,乃传统皇权思想的表现。
在实行内阁制的国家,元首一般是虚位的,只是国家的一个象征,对外代表国家,并没有什么实权,其地位是超然的,不参与政争。而在民初的内阁政治中,总统不仅参与、卷入政争,而且与内阁争权,将内阁视为古代的阁部。不论是袁世凯,还是黎元洪、冯国璋、徐世昌和曹锟,都长期受专制思想的浸润,缺乏民主观念,仍然看作是曾经的皇帝,仍然想手握各种大权,仍然具有强烈的权力欲,具有强烈的家天下的思想和帝权思想,难安于内阁制下的虚位总统,不愿受阁制的束缚,形成总统与内阁在权力上的对峙与争执,致使民初的内阁制有名无实,不能真正建立名副其实的内阁制。
可以说,“府院之争”披上了民主法制的外衣,其实质并没有超越中国传统政治中的权力斗争之本质,不过是历史上“君权”与“相权”斗争的延续,是皇权思想在共和时代的体现,双方力量存在着此消彼长的规律,即皇帝通过不断改革宰相制度,分化削减其权力,同时不断加强中央集权;同时在维持政权运行的过程中,二者既相互依存又互相排斥。
其次是《临时约法》在制度设计上对二者权力划分不清。
《临时约法》对行政、立法、司法三方面在制度上进行了分权,但其主要目的是如何在总统和内阁之间划分行政权,即如何限制总统的权力。这样,在民初政体的设计上,《临时约法》“因人立法”,将总统制改为内阁制,其标志是副署权及政府预算表决权的设置。而事实上,《临时约法》关于政体的设计既非内阁制,亦非总统制,是责任不明的双重行政体制。既然称为责任内阁制,为何又赋予总统诸多权力?如规定临时大总统代表临时政府总揽政务、公布法律(第30条)、为全国军队的最高统帅(第32条)、拥有任命官员(第34条)等权力。然而更奇怪的是,内阁须向总统而不向议会负责(第44条),这就完全背离了内阁制的基本精神,将内阁置于总统行政权的控制之下。如此即形成这样的尴尬局面:一方面内阁不是由议会中的多数派或党派联合来组织而是由总统来提名(议会批准);另一方面内阁则以副署权来对抗总统。这就导致总统和内阁的权力分配处于一种不伦不类的困境:“今日府院权限问题之难点实有大总统不负责任,而依法大总统又有总揽政务及种种职权,国务员更有负责任副署等规定”。这种体制设计就导致在总统和内阁之间经常产生权力摩擦。这种畸形的政体格局使总统、总理都据法认为自己才是最终决断者,这就导致府院摩擦不断,府院之争一再发生。
事实上,二者之间的斗争一直伴随着民国初期的政治发展,而斗争的结果则取决于总统和内阁各自代表的政治势力的消长。最初,习惯于在清廷执掌实权的袁世凯当上了民国大总统,本以为可以享受皇上的待遇,没想到,既要受到《临时约法》的约束,又要受到内阁控制,甚是不习惯,于是不甘寂寞的元首就发生了与内阁争权的局面。到帝制失败,又回归内阁制时,北京政府以黎元洪来做总统,以段祺瑞为总理,局面发生颠倒性的变化。北洋实力派代表段祺瑞自然不会听任总统府的摆布,以“责任内阁”的名义,将国务院变为真正的权力中心,总统成为盖印的工具,引起黎总统的不满。此后,府院关系均如此随着各派实力的变化而变化,其演变是传统一元权力结构的结果。袁世凯时期内阁完全被压服于总统的威权之下,而袁之后,总统又往往被运于内阁强人的股掌之间。这无疑造成了民国前期政治上无休止的混乱以及政治资源的耗损。
第三是宪政观念的缺乏。
近代以来,“以政党纲领作为组成集团的原则,这不只是用以代替个人领导的一件新事物,甚至内阁向国会负责这种思想本身也是反常的东西,因为按照儒家传统,内阁部长们同时还认为他们有效忠于国家元首的基本责任。”不论实行总统制或内阁制,当时并未建立一个深入人心的宪政体制,民国的建立仅仅是树立一个有其名而无其实的“共和”的理念,它可以对抗帝制复辟,却不足以对抗内部矛盾。如此一来,那些“共和”宪政观念十分缺乏的政客与军阀,在全新的政治领域当然是不知所措。这样的政治环境导致府院之争不断上演。同实行了几千年的专制文化相比,从西方引进的民主宪政观念实在是太弱小,以致于被淹没在专制文化的汪洋大海之中而无力求生。专制文化的丰厚和宪政观念的缺失导致这些舶来品发生变异甚至异化,走向其对立面,使中国的政治混乱不堪,甚至是引发流血和战争。
另外,政治人物的政治性格缺陷也是府院之争的一大动因。
比如,袁世凯的权力意识极强,加上长期专制的熏陶,一心想爬上权力的顶峰,一旦他当上了国家元首,就容不得挑战自己权威的人了。段祺瑞素来刚愎自用,又自恃为北洋勋宿,从内心深处对黎元洪抱轻视态度,和黎绝少交往。“段祺瑞个性特强,对于政治,重在权而不在位,平素以舍我其谁自负”。“段氏平昔性情戆直,对人对事,只要他主观认为不对,便无所顾忌。直言不讳,向来不采取阴谋暗杀手段。他是以儒、佛教的道德观念为分析事物的标准”。他作为一个典型的军人,朴素、勇敢、处事果断,作风强硬,对其心腹常常偏袒,不问是非,一惯迷信武力,不相信议会讨论对国家管理的作用。黎元洪则外柔而内刚,虽不足威慑别人,却自有不屈的意志,他“没有坚定的信念或肯定的意见,但却有按自己的主意行事的性格”,因而他出任总统时,“摩擦不是以三角形式出现,而更多地是国会与内阁之间的斗争。事实上成了因内阁的态度而发生总统与国会的摩擦,或是因总统偏向国会而发生内阁与总统之间的摩擦”。而黎元洪“朴重端慤,……木僵少文,学欠涵养,故胸无城府,惟知巩固其魁柄,大言炎炎,有时羌无实际,……性格易于冲动”。“二人性格、作风、思想迥异,对国内外事物的处理方法各执一端,不能协调一致。”因此府院之间不可能有亲密的关系,终因对德宣战而水火不容。到了冯、段执政时代,二人同属北洋系,人们本殷切期望二人“同舟共济,造福国家”,但二人性格刚硬,观点殊异,均以袁继承人自命而相争,素不融洽,时生龃龉,由朋友变为对手,发生冲突,实不可理喻,完全缺乏现代政治家的气度与素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