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首发)
一 问题的提出
揲蓍成数的占卜方法(即“筮法”)最晚产生于商代,商代晚期已经较为普遍地在使用了。进入西周以后,筮法更是和卜法一起成为最重要的两种占卜手段。通过一定的揲蓍法所得到的数,就是“筮数”。把筮数按照一定的顺序排列起来,就是“卦”。卦有两种,本文统称为“筮卦”。早期的筮卦是把所得到的一组筮数排列起来,即所谓的“数字卦”。筮数有奇、偶,后来人们按照奇数为阳、偶数为阴的观念把不同的筮数转化为两种符号,即阴爻“――”和阳爻“—”。于是数字卦逐渐演变为用阴爻和阳爻两种符号排列起来的一种新式卦,习称为“卦画”,为求明晰,本文称之为“阴阳爻卦”。很多出土材料中都记有筮卦,时间跨度从商代晚期到战国中期。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的筮卦都是数字卦,这一点学者间没有异议。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马王堆汉墓帛书以及阜阳汉简三种《周易》中的卦画都是阴阳爻卦,即今本《周易》卦画的前身,这一点学者间也没有异议。但是关于时代属于战国中期的楚国卜筮简中所记筮卦的性质,学者间却有着截然不同的两种意见。一种观点认为都是数字卦,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都是阴阳爻卦。本文谈谈我们对此问题一些不成熟的看法,供大家参考。在正式讨论之前,需要先说明以下几点:
1.楚卜筮简中记有筮卦的,有天星观简、包山简和新蔡简。后两种材料已经全部发表,是本文讨论的主要对象。另外,参考学者的相关论述和一些摹本,本文也会谨慎地涉及到天星观简。
2.为便于讨论,本文把所有筮卦中的符号统称为“卦符”。有时卦符前会标明序数,序数的排列是按照《周易》六爻的习惯从下往上数的。
3.包山卜筮简保存完整,其中6例12个卦本文全部讨论。新蔡简多残断,存有筮卦15例,我们只选取左右两卦六个卦符都完整清晰的12例24个卦进行讨论。
二 我们对于楚简所记筮卦的基本看法
我们认为楚国卜筮简所记筮卦都是数字卦。三种材料共有的筮数是“一”、“五”、“六”、“八”,分别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形。天星观简和新蔡简的筮数中还有“九”。新蔡简的筮数“九”见于零115、22左侧卦第二、第三两个卦符,其形为“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横画上靠左端“)”形的一笔清晰可辨。横画右端向下微勾,但是没有写成“九”字习见的“乙”形,大概是受上下空间限制而有所省略(筮数的写法常会比正常的数字有所简省,参看下文四)。这种写法的筮数“九”还见于张政烺先生和王明钦先生所摹天星观简的筮卦。[1]这个筮数张先生原释为“七”,不可信。“七”的写法是一长横的中间着一短竖,而该筮数的写法是在一长横上靠左端部分着一“)”形,显然是“九”。而且楚简筮数中本来就没有“七”的,详见下文五。
三 关于把楚简筮卦看作阴阳爻卦的观点的讨论
李学勤先生认为楚简中的筮卦都是阴阳爻卦,“─”即阳爻,而“╳”、“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形都是阴爻“――”变体。他说:
简上这些符号,其实不过是把表示阴爻的符号“――”写作两斜笔,又有时出现分离或者交叉而已。它们是卦画,不是数字。[2]
卦画,如众所习知,有“─”、“――”两种,一阴一阳。竹简非常狭窄,又要骈书两行,所以把“――”改为两斜笔,以避免误连。至于是连是分,或者略有交叉,信笔所之,就无须细计了。[3]
我们不同意这种看法,理由如下:
1.这种观点无法解释新蔡简和天星观简卦符中“九”的存在。
2.为便于讨论,我们把“╳”和“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称为“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按照李先生的看法,“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和“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是同一种符号,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还是“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完全是书手“信笔所之”所导致。果真是非此即彼的话,那么在足够多的卦符中,“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和“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出现概率应该大致相当才对,至少也不会过分悬殊。但是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包山简12卦72个卦符,除了“一”,还有38个,其中“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有30个,“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只有8个,相差不可谓不大。新蔡简24卦144个卦符,除了“一”和“九”,还有89个,其中“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有81个,而“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只有8个。二者出现概率的比例超过10∶1,可谓相当悬殊。这是一种表现情况。另外,如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和“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是同一种符号在书写过程中由于“信笔所之”而造成的变体,那么二者在每个卦中出现的几率也应该是平均的,也就是说如果一卦中“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和“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总数足够多,那么此二者的出现一定会呈现出随机分布的状态。然而在新蔡简24卦中,“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和“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总数在3个以上(含3个)的有18卦,却只有4卦有“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有6卦含有5个“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却没有一个“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然而乙四79中右侧卦中“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和“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总数只有3个,却有一个“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和两个“非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而且是“╳”和“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各占一个,出现概率可谓极不平衡。这是又一种表现情况。如果按照李先生的观点,单从概率统计的角度来看,以上这两种不平衡现象都是不应该出现的。
3.按照李先生的看法,“╳”、“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都是把“――”改为斜笔而形成的,那么照理说写成“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是正常的,写成“╳”和“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是偶然的,“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出现次数应该比“╳”和“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多很多才对。可是如上所述,不论是新蔡简还是包山简,“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数量都远远超过“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根据以上三个方面的情况,我们认为李先生把楚卜筮简所记筮卦看成是阴阳爻卦的观点恐怕是不能成立的。
四 关于李先生对数字卦观点的质疑的解释
李先生不同意把楚国卜筮简中的筮卦看成是数字卦,主要是出于以下三个方面的质疑:
1.所谓筮数“五”、“六”、“八”与楚简中常见的数字写法不同。前者作分别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后者分别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可见那些卦符不是筮数。[4]
2.新蔡简和包山简中的所谓筮数绝大多数都是“一”和“六”,“五”、“八”、“九”都很少见。“如果这是用某种揲蓍法产生的‘筮数’,如此不平衡的现象是不可能出现的。”[5]
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周易》和新蔡简、包山简大致是同时之物,而其阳爻作“—”,阴爻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另外王家台秦简《归藏》也是阳爻作“—”而阴爻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或“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形体都和楚卜筮简中的卦符“—”、“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非常相似。由此推论,后者也是阳爻和阴爻,而不是筮数。[6]
我们对上述三方面的质疑分别解释如下:
1.关于筮数写法和常见数字写法不同的问题。下面依次讨论“八”、“五”、“六”。
①李先生说卦符中的“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与数字“八”写法不同,这不符合实际情况。楚简中的数字“八”既有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也有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7]而楚简卦符中的“八”既有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也有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如包山简245号右侧卦第一卦符就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可见卦符中的“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就是筮数“八”。
②筮数“六”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与常见数字“六”的写法不同,这一点不独是楚简如此。从商代晚期到西周晚期,所有数字卦中的筮数“六”都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都和同时期数字“六”的写法不同。对此现象张政烺先生作过讨论,他说:
古老的写法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殷墟第一期的甲骨文中,只在“兆序”上出现,数量还不少,而通行的卜辞已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参考《甲骨文编》卷十四)。周代金文中,只在我们说的以卦为氏名的铭文中出现,通常铭文中皆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无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者(参考《金文编》卷十四)。可见“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已经变成了卜筮家的专业文字,与通行文字产生差别。[8]
可见在数字卦中把“六”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是从来如此的“惯例”。卜筮是一种神秘性的职业,所用符号的保守性和传承性都很强。我们只要看看《周易》阴爻作“――”、阳爻作“─”的形式自打定型以后历两千年无所更改,就可以明白这一点。所以楚卜筮简中的筮数“六”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是正常现象,无可怀疑。
数字“六”到了筮数里何以要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我们推测是因为“六”字常见写法“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下面两笔和“八”非常相像,为了避免混淆,就把下面两笔省去而写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了。安阳苗圃北地M80所出磨石侧面的数字卦“六六七六六八”,最下面两个筮数是“∧八”,两个筮数连在一起作“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9]极像数字“六”的常见写法“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可见我们的推测不无可能。
③李先生根据卦符“╳”与数字“五”的常见写法不同来否定“╳”是筮数,这是我们不同意的。但是王明钦先生说商周时期数字卦中“五”的写法与通常写法没有差别,[10]持论也失之片面。商周数字卦中“五”有三种写法:一种是常见的数字写法“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另一种是把“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偏转五十度的写法“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第三种就是“╳”。[11]商代数字卦中有“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也有“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但似乎很少见到“╳”。“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例子如安阳四盘磨卜骨上“八六六五八七”一卦,[12]“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例子如《邺中片羽二集》所收陶爵范上“五七六八七七”一卦。[13]西周的数字卦中似乎很少见到“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和“╳”都很多见。“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例子如凤雏H11∶7卜甲、[14]齐家T3∶28采集卜骨、[15]齐家H∶90卜骨、[16]中斿父鼎、[17]堇伯簋、[18]效父簋。[19]“╳”的例子如长安张家坡卜骨、[20]美国塞克勒博物馆藏14号圆鼎、[21]淳化石桥镇陶罐、[22]长安沣西骨镞。[23]“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例子基本上都是西周早期之物,而上揭“╳”的例子至少有一半见于西周晚期,如淳化石桥镇陶罐等。可见楚卜筮简中筮数“五”写作“╳”正是延续了西周晚期的书写习惯,无可怀疑。
数字“五”到了数字卦中为什么会出现“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或“╳”这样的写法呢?我们认为可能是因为正常写法“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上下各有一横,容易和“一”混淆,所以才有把“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侧过来的写法“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和省去上下两横的写法“╳”。商周数字卦中所有与“一”相连的“五”全部都是“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或“╳”,没有一例“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见上揭张家坡卜骨、堇伯簋、赛克勒博物馆藏14号鼎、石桥镇陶罐、沣西骨镞),正说明了这一点。
2.关于筮数中“一”、“六”特别多的质疑。其实学者早就发现商人数字卦中出现最多的是“六”、“七”,而周人数字卦中出现最多的是“一”、“六”(详见下文五)。[24]我们统计了32例典型的周人六卦符数字卦(所谓“典型的周人数字卦”,参看下文五)中各个筮数出现的次数,列表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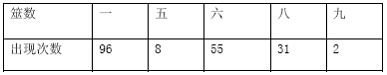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
可见筮数“一”、“六”特别多本来就是周人数字卦的特点,所以楚卜筮简中“一”、“六”远远多于其它筮数的现象并无可疑之处。
关于周人数字卦“一”、“六”特别多的原因,张政烺先生有一个解释。数字卦中从不见“二”、“三”、“亖(四)”,张先生认为这是由于“二”、“三”、“亖(四)”都是积横画为之,容易混淆,于是逢“三”则变“一”,逢“二”、“亖(四)”则变“六”,[25]“所以‘六’和‘一’这两个数目字在卦爻里就特别多了”。[26]这个意见无疑是很有道理的。
李先生认为楚卜筮简中“一”、“六”极多而“八”、“五”极少,“这样不平衡的分布,仍是揲蓍法难于产生的”。[27]我们认为新蔡简24卦144个卦符,包山简12卦72个卦符,似乎已经很多。可是出现哪个筮数至少有“一”、“五”、“六”、“八”、“九”五种可能,五种可能性放在144或72个总数中,出现分布不平衡的现象当然是概率所允许的。但是所得筮数是奇数还是偶数的可能性却只有两种,其出现概率应该是较为平衡的。换句话说,概率统计所决定的平衡性,不能于具体筮数求之(因为可能性太多),而却能于奇、偶求之(因为只有两种可能性,非此即彼)。新蔡简144个筮数中,奇数58个,偶数86个,相差不能算大(还应考虑到新蔡简残缺不全的因素)。而包山简72个筮数中,奇数35个,偶数37个,可以说相当平衡。
3.上海博物馆藏战国竹书《周易》中的卦符“一”和“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毫无疑问是阳爻和阴爻,但这与楚卜筮简中的筮卦是数字卦并不矛盾。《周易》虽然只有64卦384爻,但是辅之以卦变和互体等手段,足以应付实际筮占时的各种复杂情况。所以其卦符可以采用具有一般性的阴阳爻来表示,因为《周易》本来就是一部可以以简驭繁的筮占工具书。但是在实际进行筮占的时候,不论所得是阴爻还是阳爻,都必然对应于一个具体的筮数,这是显而易见的。比如按照后人所传揲蓍法(见朱熹《周易本义》卷首《筮仪》),筮数必然是“九”、“八”、“七”、“六”之一。阳数“九”变“七”不变,阴数“六”变“八”不变。举例说,如果筮得《否》之《遯》,《否》卦“六三”变为“九三”。即便否卦的第三爻用阴爻“――”来记录,人们也会知道第三爻实际占得的筮数是“六”而不是“八”。楚卜筮简所记筮卦都是当时实际筮占所得之卦,可能楚人的习惯就是按实得之数记录实得之卦,这样卦中的吉凶消息可以一目了然,而且也便于日后查考。所以说楚卜筮简用数字卦的形式记录当时实得之卦,与《周易》这样用阴阳爻作卦符的筮占工具书同时并存,并没有矛盾之处。很多学者都认为《周易》的阴阳爻是从数字卦中的“一”、“六”或“八”那里演变而来,我们同意这种看法,并且认为二者在实际生活中各司其职,并不矛盾。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楚卜筮简所记筮卦都是数字卦,学者对于这种观点的种种质疑及其认为楚卜筮简所记筮卦为阴阳爻卦的观点都是很难成立的。
五 余论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想在这里讨论一下。
过去很多学者常常是把商周数字卦笼统地放在一起加以统计讨论,李学勤先生首先注意到这些数字卦按其筮数出现次数的多寡可以分为两类。他说:
上述商代、西周的揲蓍法一定有所不同。淳化陶罐、扶风和沣西卜骨筮数所代表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一,其次六、八,少见五、九,没有七,可暂称为揲蓍法乙。殷墟甲骨、陶器、岐山卜甲和西周金文筮书所代表的揲蓍法最容易出现六,其次七、八,少见一、五、九,可暂称为揲蓍法甲。有没有“七”,是区别甲、乙两种揲蓍法的标志,这大约是在揲蓍法乙中“七”极难或不能产生之故。[28]
受李先生文章的启发,我们重新考察了相关材料,发现商周两代的数字卦实际上都可以分成两类:甲类出现次数最多的筮数是“六”、“七”、“八”,乙类出现次数最多的筮数是“一”、“六”、“八”。商代数字卦绝大多数都属于甲类,例如安阳四盘磨卜骨、小屯南地易卦卜甲、[29]大司空村陶簋、[30]苗圃北地磨石正面和侧面、[31]《邺中片羽二集》所收陶爵范,等等。也有个别数字卦属于乙类,例如山东平阴朱家桥陶罐、[32]苗圃北地磨石背面,[33]等等。西周数字卦中属于甲类的有:岐山凤雏H∶11卜甲、[34]扶风齐家H∶90卜骨、房山镇江营卜骨、[35]中方鼎、召仲卣、父乙盉,等等。属于乙类的有:长安张家坡卜骨、沣西卜骨、[36]扶风齐家T3∶28采集卜骨、召卣、[37]岐山贺家村M113铜甗、[38]美国赛克勒博物馆藏14号圆鼎及121号盘、[39]淳化县石桥镇陶罐、长安县西仁村采集陶拍,[40]等等。
仔细分析上述材料,可以看到商代数字卦中甲类占绝大多数,周代数字卦中则是乙类远多于甲类。并且西周甲类所在的材料时代都比较早,而且与商人有关,如凤雏H∶11卜甲等;而西周晚期的材料中又只有乙类。这样我们可以推断甲类代表着商人的特色,而乙类代表着周人的特色。甲类和乙类的区别正如李学勤先生所说,在于筮数“七”的有无。但是这种不同的实质,与其说是揲蓍法的不同,我们觉得还不如说是商、周筮法的不同。周人筮数无“七”,并非因为其所用揲蓍法揲不出“七”,而是由于周人筮法不占“七”的缘故。所以逢“七”就变“一”,就像张政烺先生推断的逢“三”变“一”一样(参看上文)。若此说可信,就更加说明了从西周到战国的数字卦中何以“一”特别的多的缘由。而商人筮数多“七”,也不是因为其所用揲蓍法容易揲出“七”来,而是由于商人筮法占“七”的缘故。文献记载《连山》、《归藏》为夏、商之《易》,皆以“七”、“八”为占。[41]现在看来,至少说商人以“七”为占恐怕还是有根据的。
放大了说,商、周筮法的不同,其实也就是当时东、西方筮法的不同。张政烺先生认为东、西方筮法的不同在于西方用“九”而东方不用“九”,[42]是由于受当时材料所限而没有在商人的数字卦中找到“九”。实际上商人数字卦中是有“九”的,见于上面提到的殷墟小屯南地发现的一片卜甲。[43]现在看来,东、西方筮法的不同实在于东方用“七”而西方不用“七”。这个传统一直延续到战国,所以我们在楚国卜筮简的数字卦中也见不到“七”。过去以为天星观简的筮数中有“七”,其实是“九”的误认(参看上文二)。于此可见楚卜筮简的数字卦不但筮数的写法和西周相同,筮法也是一脉相承的。
古代贵族进行筮占的时候常常会杂用不同的筮法,[44]下面三个文献中的例子是大家所熟悉的:
①公子亲筮之,曰:“尚有晋国。”得贞《屯》悔《豫》,皆八也。(《国语•晋语四》)
②臣筮之,得《泰》之八。(同上)
③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左传•襄公九年》)
据历代学者研究,以上三例都是杂用三《易》进行筮占的例子。[45]在上揭出土数字卦的材料中,有材料属商而用西方筮法的例子,也有材料属周而用东方筮法的例子。前者如山东平阴朱家桥陶罐,后者如岐山凤雏H∶11卜甲、扶风齐家H∶90卜骨、房山镇江营卜骨、中方鼎、召仲卣、父乙盉等。更有同一种材料上两种筮法并存的例子,如安阳苗圃北地磨石正面、侧面的数字卦都是商人风格,而背面的数字卦却是周人的风格,这正是使用了不同的筮法的缘故。
关于周原刻辞甲骨的来源,已有很多学者做过讨论,主要有“周原本土占卜说”和“卜后移来周原说”两种意见。[46]从凤雏H∶11卜甲和齐家H∶90卜骨上数字卦显示的筮法来看,它们本在商人地域内施用然后被带回周原的可能性还是存在的。也有可能是在周原本地进行筮占,只是用的是商人的筮法而已。商文化对周人影响很大,周人有时采用商人的筮法是可能的。当然,也有可能主持筮占的就是自商投奔周人而来的史官一类的人。
(编者按:[1]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697页讼卦第二卦符,中华书局,2004年4月。王明钦:《湖北江陵天星观楚简的初步研究》48页150号,北京大学硕士学位论文,1989年5月。
[2]李学勤:《论战国简的卦画》,《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12月。又,氏著《周易溯源》283页,巴蜀书社,2006年1月。
[3]李学勤:《出土筮数与三易研究》,见氏著《重写学术史》394页,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1月。又,氏著《周易溯源》277页。
[4]李学勤:《周易溯源》283页。
[5]李学勤:《周易溯源》282页。
[6]李学勤:《论战国简的卦画》,《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4~5页。又,氏著《周易溯源》283~284页。
[7]参看李守奎《楚文字编》51—52页,867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12月。又张胜波《新蔡葛陵楚墓竹简文字编》17页,151页,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6年5月。
[8]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683页。
[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2期,118页,图一一∶2。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2期,49页,图二。
[10]王明钦:《试论〈归藏〉的几个问题》,《一剑集》105页,中国妇女出版社,1996年10月。
[11]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562—566页。563页例九的“五”应该是“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误为“

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了。
[12]《中国考古学报》1951年第5册图版肆壹。曹定云:《殷墟四盘磨“易卦”卜骨研究》,《考古》1989年7期638页图一。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694页图五。
[13]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565页例二八,699页图八。
[14]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18页,388页,三秦出版社,1991年。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图版58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9月。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694页图三。
[15]罗西章、王均显:《周原扶风地区出土西周甲骨的初步认识》,《文物》1987年2期21页图八,图版叁:4 。 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124页,446页。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267页,图六五,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696页图七。
[16]曹玮:《周原新出西周甲骨文研究》,《考古与文物》2003年2期,45页,图五,图六。
[17]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3·18·4,中华书局,1983年12月。
[18]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6·39·5。
[19]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3·46·3。
[20]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长安张家坡村西周遗址的重要发现》,《文物参考资料》1956年3期,40页,图一,图二。唐兰:《在甲骨金文中所见的一种已经遗失的中国古代文字》,《考古学报》1957年2期,34页,图一。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699页图九。
[21]Jessica Rawson,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Vol.ⅡB,No.14.
[22]姚生民:《淳化县发现西周易卦符号文字陶罐》,《文博》1990年3期,56页,图三,图四。
[23]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92页图六○∶13,图版肆玖∶12,文物出版社,1963年3月。
[24]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68~172页,长春出版社,1992年8月。又,氏著《周易溯源》228~233页。
[25]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682页,695页,720页。
[26]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682页。
[27]李学勤:《论战国简的卦画》,《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4页。又,氏著《周易溯源》283页。
[28]李学勤:《周易经传溯源》170~171页。又,氏著《周易溯源》231页。
[29]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1期67页图一,图二,图版八。
[30]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发掘队:《1958—1959年殷墟发掘简报》,《考古》1961年2期,74页,图一二∶2、3。
[3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2期,118页,图一一∶1、2。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2期,49页,图二,图三。
[32]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东发掘队:《山东平阴县朱家桥殷代遗址》,《考古》1961年2期,93页,图九∶8。
[33]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1980—1982年安阳苗圃北地遗址发掘简报》,《考古》1986年2期,118页,图一一∶3。郑若葵:《安阳苗圃北地新发现的殷代刻数石器及相关问题》,《文物》1986年2期,49页,图四。
[34]徐锡台:《周原甲骨文综述》18、56、60、62、63、92、388、411、413、415页。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图版58页,107~108页。
[35]李学勤:《周易溯源》240~242页。
[36]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沣西发掘报告》111页图七○,图版陆叁∶4。
[37]罗振玉:《三代吉金文存》12·45·1。
[38]陈全方:《周原与周文化》图版7页。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694页图六。
[39]Jessica Rawson,Western Zhou Ritual Bronzes from the Arthur M.Sackler Collections,Havard University Press,1990,Vol.ⅡB,No.121.
[40]曹玮:《陶拍上的数字卦研究》,《文物》2002年11期,图一—,图一二。
[41]见《左传·襄公九年》“遇艮之八”下杜预注和孔颖达疏,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1942页上,中华书局,1980年9月。
[42]张政烺:《张政烺文史论集》682~684页,695~696页。
[43]肖楠:《安阳殷墟发现“易卦”卜甲》,《考古》1989年1期67页图一,图二,图版八。李零:《中国方术考(修订本)》257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4月。李零:《中国方术续考》309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
[44]李零:《中国方术续考》315—316页,东方出版社,2000年10月。
[45]徐元诰:《国语集解(修订本)》340页,中华书局,2006年4月。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下册1942页上。
[46]王宇信、杨升南主编:《甲骨学一百年》308—327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9月。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921.html
以上是关于阴阳先生-楚简数字卦的再讨论(稿)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