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卦方位-论秦简“日夕分”爲地平方位数据 ,对于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来说,八卦方位-论秦简“日夕分”爲地平方位数据是一个非常想了解的问题,下面小编就带领大家看看这个问题。
原文标题:论秦简“日夕分”爲地平方位数据
(中国科学院国家天文台)
[摘 要] 云梦睡虎地、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中的“日夕(夜)分”数不是等间距十六时制的数据,而是根据日出入方位授时的地平方位数据。秦汉《颛顼曆》根据“日夕分”决定“昼夜刻”的原理,使用“九日增减一刻”的经验算法计算昼夜长短;东汉以后改用晷漏算法,遂使“日夕分”方法湮没无闻。
[关键词] 秦简《日书》 日夕分 《颛顼曆》 昼夜长短
云梦睡虎地秦简《日书》(甲、乙种)中有三份相同的日夕数表[1]:
正月日七夕九,二月日八夕八,
三月日九夕七,四月日十夕六,
五月日十一夕五,六月日十夕六,
七月日九夕七,八月日八夕八,
九月日七夕九,十月日六夕十,
十一月日五夕十一,十二月日六夕十。
于豪亮先生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首先提出它是一份各月昼夜长短的表,昼夜的总和正是十六时,幷指出秦汉时幷行两种记时制,即曆法家的十二时制和民间的十六时制[2]。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记有同样数字、仅将“夕”改成“夜”字的日夜数表[3]。放马滩秦简《日书甲种》的《生子》章还完整地列出了自“平旦”、“日出”到“鶏鸣”等十六个时辰的名称,成爲秦行十六时制的重要证据[4]。近年张德芳先生引居延汉简记载当时规定公文书信送达以“一时行十里”、“一日一夜当行百六十里”爲标準,作爲秦时实行等间距十六时制的有力证据[5]。于是秦汉时期曾经实行等时制的十六时制几成定论[6],笔者也曾经有过类似的主张[7]。然而这一说法是有问题的。近来笔者利用现代天文学中的球面天文学公式,对秦简“日夕分”数据与典籍中的“昼夜刻”数据,进行计算分析,发现两者有明显区别,秦简“日夕分”数据与地平式日晷的日出方位角相符合,而“昼夜刻”数据则与中原地区的昼夜长短变化基本符合。
1 “日夕分”、“昼夜刻”与方位角、时角
首先,与秦简日夕(夜)数表相同的数踞,还见于东汉王充《论衡·说日篇》,此段文字多被论者引证,以作爲汉行十六时制的证据,但我仔细分析原文,发现与十六时制幷无关係,兹引如下:
问曰:“当夏五月日长之时在东井,东井近极,故日道长。今案察五月之时,日出于寅,入于戌。日道长,去人远,何以得见其出于寅入于戌乎?”日东井之时,去人、极近。夫东井近极,若极旋转,人常见之矣。使东井在极旁侧,得无夜常爲昼乎!日昼行十六分,人常见之,不复出入焉。儒者或曰:“日月有九道,故曰日行有近远,昼夜有长短也。”夫复五月之时,昼十一分,夜五分;六月,昼十分,夜六分;从六月往至十一月,月减一分。此则日行月从一分道也,岁日行天十六道也,岂徒九道?
原文前后两个问题讨论的都是日出入方位问题。第一个问题是关于冬至日出入方位的问题,提问人的意思是说:夏至日在东井,离极近、去人远,那麽太阳应在恒显圈内终日不落(“昼行十六分”),不存在日出入的问题——爲什麽说夏至太阳出于寅、入于戌呢?王充回答:因爲日在东井时,相对其它节气离北极较近,但离人也很近(把日光直射看作近、斜射看作远),不会出现永昼现象,因而太阳在地平圈上出寅入戌。
第二个问题是关于日出入方位与昼夜长短的问题。儒者提出日行九道,每行一道去极有近远,这是引起昼夜长短变化的原因。“九道术”今不传,从文意可以推知是指天球上南北回归綫之间平均分布的九个纬圈。太阳于不同季节在这些纬圈上东升西落,纬圈与地平圈相交处就是日出入方位。因此“日行远近”与昼夜长短的关係,实际上是日出入方位与季节的关係。王充把昼夜长短变化推广到极端——从永昼到永夜的情况:设定地平圈平分爲十六等分,从日“昼行十六分”(永昼)到夜行十六分(永夜),一年内每一分道都有可能成爲日出入方位(“岁日行天十六道也”),岂只九道!
王充的推论完全超出人们的经验之外,在理论上是非常正确的;但他仍然给出经验观察值“今案察五月之时……昼十一分,夜五分”等等,这实际上是地平圈上昼弧与夜弧长度之比,它与时角圈上的昼、夜弧之比完全是两回事——前者是地平方位数据,后者是赤道时角数据,对应于现代不同的坐标系统。如下图所示:太阳的时角与方位角分别属于赤道坐标系与地平坐标系。地平坐标系以天顶爲极、以地平圈爲基圈;时角坐标系又称第二赤道坐标系,以北极爲极、以时角圈(赤道)爲基圈。由于坐标系的极和基圈都不相同,当地平方位取等分间隔时,所对应的时角必定是不等分的即不等时的。因此,根据王充《论衡》的表述,我们还是把秦简《日书》的昼夜十六等分称之爲“十六分”制,而不称爲“十六时”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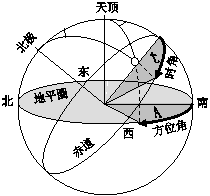
八卦方位-论秦简“日夕分”爲地平方位数据
时角与方位角示意图
其次,论者引多《淮南子·天文训》的一日十五个时段(加“夜半”爲十六时)作爲汉行十六时制的证明。实则《天文训》讲的是太阳方位与时称的关係。每一个时称对应一个方位地名,如早晨对应东方的旸谷、曲阿等,中午对应南方的衡阳、昆吾等,傍晚对应西方的虞渊、蒙穀等。其文曰“日入于虞渊之汜,曙于蒙穀之浦,行九州七舍,有五亿万七千三百九里,离以爲朝昼昏夜。”直接给出当时人们认爲太阳所绕行的地平圈(九州七舍)的总周长;“离以爲朝、昼、昏、夜”才是指与漏刻数相关的时间。高诱注:“自阳谷至虞渊,凡十六所,爲九州七舍也。”清钱塘撰《淮南天文训补注》[8],将“九州七舍”与王充所说“十六道”联繫起来,幷作“日行十六道合堪舆之图”以明其事。此所谓“堪舆”就是指的地平方位,在这点上钱塘对“十六道”的理解是正确的,幷根据《周脾算经》中四时日出入方位计算《论衡》的昼夜分,两者符合得非常好。但他仍然没有把时角和方位角区分开来,因此结论是错误的。钱塘对高诱注作补注曰:“王充所说十六道,与此十六所合。然则此即漏刻矣。日有百刻,以十六约之,积六刻百分刻之二十五而爲一所。二分昼夜平,各行八所;二至昼夜短长极,则或十一与五。而分、至之间,以此爲率而损益焉。”钱塘既说十六道“合堪舆”(方位),又说“即漏刻”(时角),自相矛盾而不知。
第三,与王充同时代幷行的后汉《四分曆》列有二十四节气的昼夜漏刻数,其昼夜刻之比与秦简日夕分在数值上不合。《四分曆》昼夜共百刻,冬至昼漏四十五刻,夜漏五十五刻;夏至昼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二至之间相差二十刻,依次增损。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五引梁《漏刻经》云“至冬至,昼漏四十五刻。冬至之后日长,九日加一刻。以至夏至,昼漏六十五刻。夏至之后日短,九日减一刻。或秦之遗法,汉代施用。”又引《元嘉起居注》曰:“以日出入定昼夜。冬至昼四十刻;夏至夜亦宜四十刻,夏至昼六十刻,冬至夜亦宜六十刻。春秋分,昼夜各五十刻。今减夜限,日出前,日入后,昏明际,各二刻半以益昼。夏至昼六十五刻,冬至昼四十五刻,二分昼五十五刻而已。”唐孔颖达《尚书·尧典正义》称“天之昼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昼夜以昏明爲限”,幷引东汉马融“据日出见爲说”云:“古制刻漏昼夜百刻。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刻。昼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孔颖达称此爲“古今曆术……不易之法也”。《礼记·月令》孙希旦集解:“大史漏刻,夏至昼漏六十五刻,夜漏三十五刻。愚谓以昏明爲限,则夏至昼六十五刻,夜三十五刻;以日之出入爲限,则昼六十刻,夜四十刻也。”《隋书·天文志上》“冬至昼漏四十刻,夜漏六十刻;夏至昼漏六十刻,夜漏四十刻;春秋二分,昼夜各五十刻。日未出前二刻半而明,既没后二刻半乃昏。减夜五刻,以益昼漏,谓之昏旦。漏刻皆随气增损,冬夏二至之间,昼夜长短凡差二十刻。”
据上引文献,有两种昼夜漏刻数据,一种是昏明爲界限的“昼夜漏”数据——“夏至昼六十五刻,冬至昼四十五刻”;另一种是以日出入爲爲界限的“昼夜刻”数据——“(夏至)昼长六十刻”,“(冬至)昼短四十刻”。后者是马融所说的“古制”,大约是相对于前者《四分曆》的“今制”而言。但实际上它们都是关于“昼夜长短”变化的同一数据,只是由于对昼夜界限的定义不同,在数值上加减昏旦长度而形成差异,其适用时代与地域是一样的。据研究,《四分曆》的黄道去极、晷影、漏刻数表与实际观测(公元100年、洛阳纬度34º43′)符合得很好[9]。其时代与梁《漏刻经》所云“或秦之遗法,汉代施用”亦相符合。
但无论是“古制”漏刻,还是《四分曆》的“昼夜刻”,它们所代表的真正昼夜长短变化值,与秦简《日书》中的十六分“日夜数”相差很大。秦简《日书》中的十六分日夜数,同样是“秦之遗法,汉代施用”,其昼弧极大值(11/16=68.75/100),比《四分曆》的日出入昼长极大值(60/100)要长8.75﹪,化算爲时间则相差2.1小时,这是不能用误差来解释的。这反证秦简日夕数不是时间数据。
如果以秦简“日夕分”爲地平昼夜弧,与秦汉地平式日晷上的昼夜弧比较,问题迎刃而解。日晷正面上的圆周等分爲100分,有放射性条纹1~69条(占68分),代表地平昼夜弧的极大值;余32分空白代表地平昼夜弧的极小值,两者与相应的秦简日夕分在百分数的整数部分完全相等,即
11/16≈68﹪, 5/16≈32﹪
这一数据表明,秦简“日夕分“与地平式日晷上的刻分性质相同,反映的都是地平方位数据。此外秦简日夕分作爲地平数据,还与安徽含山淩家滩新时期时代玉版上可能爲天文准綫所等分的地平数据完全相同[10],近年来在山西襄汾陶寺新石器时代城址发现4100多年前根据日出入方位授时的古观象台遗迹等[11],表明日出入方位授时在中国有非常古老的传统。
2 “十六时”非等时制
那麽,秦简“十六分”与“十六时”有何关係呢?这与“十二辰”到“十二时”的关係是雷同的。“十二辰”原本是地平方位,等分地平圈爲十二分,以十二地支命名。根据两种太阳方位——日出某辰,日加某辰,分别用于日出入方位授时和太阳方位计时。日出某辰表示太阳正好交于地平圈的方位,用以划分一年之内的节气;日加某辰表示任一高度太阳垂直对应于地平圈上的方位,用以划分一日之内的时辰。例如成书于两汉之际的《周髀算经》用“日加酉之时”、“日加卯之时”等表示太阳在某时刻加于某辰位,人们或者去掉“日加”字样,省称爲“酉时”、“卯时”等,即所谓“十二时”。这样一来“十二辰”与“十二时”就没有区别,合称爲“十二时辰”了,原来的“平旦”“日出”“夜半”“鶏鸣”等实际意义也被太阳方位(十二支)所取代。前文揭明基于等分的方位不可能得到等分的时角,因此十二“加时”不可能是等间距计时。类似地,“十六时”也是日行“九州七舍”的“加时”,同样不可能是等时的。
真正的等时制是漏刻制。但漏刻计时的序数太大,将百刻分爲昼、夜漏有40~60刻,再使用倒数“昼漏(或夜漏)未尽若干刻”也达到20~30刻,使用不便[12];而且其起算点昏终旦始时刻随季节变化而不固定,使得不同时日同名时刻的早晚难于比较,因此将“十二时”等时化是一个合理的选择。问题是将昼夜百刻平均分配给十二辰时不能使每一时辰拥有整数刻,于是政府有时会调整昼夜漏刻的总数,以使“一辰有全刻”。例如《汉书·哀帝纪》及《李寻传》载哀帝下诏“以建平二年(公元前5年)爲太初元年……漏刻以百二十爲度,布告天下,使明知之。”顔师古注:“旧漏昼夜其百刻,今增其二十。”其目的显然是爲了使一辰平均拥有十二刻。虽然新法“寻亦寝废”,百刻制很快被恢复,但据新辰刻分配法的昙花一现,可以推断大约至迟在西汉晚期,“十二时”已向等时制过渡。此时的“平旦”、“日出”等不再具有实际意义,而只是等间距十二时辰的代名词。河西敦煌、居延等汉简中的十二时可以肯定爲等时制,而先秦时代、秦汉之际包括秦简《日书》中的十二时是否爲等时制尚须严格证明。
至于所谓“十六时”的情况,则比较複杂。《淮南子》所载十五时是比较明确的太阳方位计时,仅给“夜半”留了一个时称的空位,但放马滩秦简《日书》[13]的十六时中相当于“夜半”的时段却分爲“夜未中”、“夜中”、“夜过中”三个时称;《黄帝内经素问》的十六时也有“合夜”、“夜半”、“夜半后”三个时称;陈梦家先生主张汉代官方实行十八时制[14],其夜半分爲“夜少半”、“夜半”、“夜大半”共三个时段。若将“夜半三分”合而爲一,则陈梦家的十八时就变成了十六时,而秦简《日书》及《内经素问》就不是十六时了。悬泉汉简有一木牍记录一昼夜32个时称[15],如夜半被分爲“夜少半”、“夜过少半”、“夜几半”、“夜半”、“过半”、“夜大半”六个时称,鶏鸣被分爲“鶏前鸣”、“中鸣”、“后鸣”三个时称等,表明幷非由16时平分爲32小时而来;不仅如此,在居延和敦煌用于记时的其它时称还有近20个,两者加起来共52个称谓[16]。这种混乱的情况很难想像与等间距十六时联繫起来,还不如称爲全和钧先生所谓“自然特徵计时”[17]、宋镇豪先生所谓“分段纪时”[18]等比较妥当。至于居延汉简关于“一日一夜当行百六十里”的规定,可能是个大概平均数,不一定要作等时制解释。
荆州关沮周家台秦汉墓出土简牍有一幅二十八小时与二十八宿对照图[19],如其夜半被分爲“夜三分之一”、“夜未半”、“夜半”、“夜过半”四小时,鶏鸣被分爲“鶏未鸣”、“鶏前鸣”、“鶏后鸣”三小时等。这种分布可能是一种二十八宿“值时”的式占法,与睡虎地秦简中的二十八宿“值日”法相类似,应与等时制或星在位置无实际关係。
3 《颛顼曆》的“日夕分”与“昼夜刻”
秦简日夕数虽然不等于昼夜长短数,但它与昼夜长短相关,现代天文学知识告诉我们两者呈三角函数关係。古人虽不知其精确定量关係,然据经验观测可知其定性关係,即昼夜长短随日夕数消长而增损,幷建立了半定量的经验公式或数表。已知日夕分就可以推算或查表得漏刻数,已知昼夜漏刻就可以在昏终、旦始时刻观测中星距度,由昏旦中星可以推算日所在二十八宿距度,于是形成一套“日夕分——昼夜漏——昏旦中星——日所在”等较爲完备的曆法体系。因此秦简日夕分是曆法的基本数据,秦及西汉前期施行《颛顼曆》,可以断定它是《颛顼曆》(小正)的基本法数。
现在我们可以复原《颛顼曆》的“日夕分”与“昼夜刻”数值对照表。如前引马融关于“古制”二至二分的漏刻数爲:
昼长六十刻,夜短四十刻;
昼短四十刻,夜长六十刻;
昼中五十刻,夜亦五十刻。
此“古制”可与秦简五月、十一月及二月、八月的“日夕数”相对应,以爲《颛顼曆》的两种基本法数。又按“官漏”九日增减一刻的古制,四立距分至各四十五日余(《淮南子·天文训》“距日冬至四十五日而立春”云云),五九四十五,故在分至昼夜刻上加减五刻即得立春、立夏、立秋、立冬的昼夜刻,使得分至啓闭昼夜皆得整数刻。不过四立昼夜刻不对应于“月减一分”的日夕数,而对应其相应的半数。其它“日夕分”对应的昼夜刻可在分至数值间进行一次内插得到,列如下表。
《颛顼曆》“日夕分”与“昼夜刻”对照表
中气
月份
日夕分
昼夜刻
日分
夕分
昼刻
夜刻
雨水
正月
7
9
46 2/3
53 1/3
春分
二月
8
8
50
50
穀雨
三月
9
7
53 1/3
46 2/3
小满
四月
10
6
56 2/3
43 1/3
夏至
五月
11
5
60
40
大暑
六月
10
6
56 2/3
43 1/3
处暑
七月
9
7
53 1/3
46 2/3
秋分
八月
8
8
50
50
霜降
九月
7
9
46 2/3
53 1/3
小雪
十月
6
10
43 1/3
56 2/3
冬至
十一月
5
11
40
60
大寒
十二月
6
10
43 1/3
56 2/3
《颛顼曆》的漏刻法经过汉武帝时期的整理,到东汉早期仍施用,被称爲“官漏”。李淳风《隋书·天文志上》载:“刘向《洪範传》记武帝时所用法云:‘冬夏二至之间,一百八十余日,昼夜差二十刻。’大率二至之后,九日而增损一刻焉。”唐徐坚《初学记》卷二十五引梁《漏刻经》云:“冬至之后日长,九日加一刻……夏至之后日短,九日减一刻。或秦之遗法,汉代施用。”这种所谓“秦之遗法”理当与秦简“日夕分”属于同一曆法系统。由于“日夕分”属于地平数据,我们有理由推断这一系统出自盖天家。
东汉和帝永元年间,对漏刻制度进行了一次重大改革,浑天家的晷景漏刻制取代了“九日增减一刻”的官漏[20]。司马彪《续汉书·律曆志中》有载,爲便于分析,详引如下:
永元十四年(102年),待诏太史霍融上言:“官漏刻率九日增减一刻,不与天相应,或时差至二刻半,不如《夏曆》密。”诏书下太常,令史官与(霍)融以仪校天,课度远近.
太史令舒、(卫)承、(李)梵等对:“案官所施漏法《令甲》第六《常符漏品》,孝宣皇帝三年(前71年)十二月乙酉下,建武十年(34年)二月壬午诏书施行。漏刻以日长短爲数,率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减一刻。一气俱十五日,日去极各有多少。今官漏率九日移一刻,不随日进退。《夏曆》漏刻随日南北爲长短,密近于官漏,分明可施行。”
其年十一月甲寅,诏曰:“……今官漏以计率分昏明,九日增减一刻,违失其实,至爲疏数以祸法。太史待诏霍融上言,不与天相应。太常史官,运仪下水,官漏失天者至三刻。以晷景爲刻,少所违失,密近有验。今下晷景、漏刻四十八箭,立成斧,官府当用者,计吏到,班予四十八箭。”文多,故魁取二十四日所在,幷黄道去极、晷景、漏刻、昏明中星刻于下。
霍融推荐幷获得实行的“《夏曆》漏刻”有两大特点:一是“以晷景爲刻”,即由晷影长决定昼夜刻,以取代由日夕分决定的漏刻;二是“日南北二度四分而增减一刻”,即由日在黄道上的去极度增减二度四分决定昼夜漏增减一刻,以取代九日增减一刻。两者是关联的,因爲黄道去极度——太阳赤纬的余角,是由正午时的太阳高度换算得来的,而正午时的影长就是晷景。据《周髀算经》载当时测得黄赤夹角爲二十四度,南北合四十八度,按一度换一漏箭得四十八箭;按二度四分增减一刻得二至昼夜差二十刻。仅“昼夜差”与“秦之遗法”略同外,《夏曆》主要法术已根本改变,形成“晷影长——黄道去极——昼夜漏——昏旦中星——日所在”等新一套曆法的算法系统。“黄道去极度”是浑天说使用的基本概念,因此这一系统是浑天家的赤道系统。
《夏曆》晷漏算法的实质是据太阳赤纬定节气,可称爲赤道方法;《颛顼曆》日夕分漏刻算法的实质是据日出入方位定节气,可称爲地平方法。两者在天文学原理上幷无优劣之分,但在具体算法上却有高下之别。《夏曆》漏刻“随日南北(赤纬变化)爲长短”,故“密近有验”;而《颛顼曆》官漏可能出于分至啓闭皆得全刻的考虑给出“九日增减一刻”的经验算法,误差达2.5~3刻,因而在竞争中败给了《夏曆》。后汉《四分曆》的主要作者之一李梵参与了这一漏刻改革的全过程,故《四分曆》采用晷漏算法,幷爲此后历代曆法家所继承。日夕分算法从此退出历史舞台,以致湮没无闻。我们今天面对出土的日夕分数据出现错误理解就毫不奇怪了。
4 其它地平方位数据
文献典籍中不乏有日出入方位与季节关係的记载。《周髀算经》卷下之三:
冬至昼极短,日出辰而入申,阳照三,不覆九。……夏至昼极长,日出寅而入戌,阳照九,不覆三。
这是一套“十二分”日夕数,与秦简“十六分”日夕数分属不同的曆法派别。这套“日夕分”数据既出自《周髀》,当与周朝有关,很可能出自“古六曆”中的《周曆》或者《鲁曆》,属于曆法中的“天正”派别;秦简“十六分”日夕数可能出自《颛顼曆》或《夏曆》,属于曆法中的“人正”派别。两套“日夕分”数据的最大差值在冬至(或夏至)的昼长值,等于十六分之一(5/16 - 3/12 = 1/16),合百刻制的6.25刻,这可能是由不同的“日出”、“日入”定义引起的[21]。
天正《周曆》的日出入大约是以昏终旦始爲昼夜界限的,故当在人正《颛顼曆》的基础上“减夜五刻以益昼漏”,得天正二至“昼夜漏”长短爲六十五刻对三十五刻。据曆法而言,天正昼夜、人正昼夜,与孔颖达注《尧典》所称“天之昼夜以日出入爲分,人之昼夜以昏明爲限”正好相反。据上所论,可复原《周髀》给出的“日夕分”与“昼夜漏”数值对照表:
冬至日三、夕九分,对应昼漏四十五、夜漏五十五刻;
春秋分日六、夕六分,对应昼漏五十五、夜漏四十五刻;
夏至日九、夕三分,对应昼漏六十五、夜漏三十五刻。
其它节气的“日夕分”与“昼夜漏”数值可据上述三个定点由一次内插法得出。
后世有人继续探讨方位与时间的关係。《隋书·天文志》载开皇十四年(594年)鄜州司马袁充“以短影平仪(地平式日晷),均布十二辰,立表,随日影所指辰刻,以验漏水之节。十二辰刻,互有多少,时正前后,刻亦不同”。其二至二分“辰刻之法”爲:
冬至:日出辰正,入申正,昼四十刻,夜六十刻。子、丑、亥各二刻,寅、戌各六刻,卯、酉各十三刻,辰、申各十四刻,巳、未各十刻,午八刻;
春秋二分:日出卯正,入酉正,昼五十刻,夜五十刻。子四刻,丑、亥七刻,寅、戌九刻,卯、酉十四刻,辰、申九刻,巳、未七刻,午四刻;
夏至:日出寅正,入戌正,昼六十刻,夜四十刻。子八刻,丑、亥十刻,寅、戌十四刻,卯、酉十三刻,辰、申六刻,巳、未二刻,午二刻。
袁充实际给出一份“日夕分”与“昼夜刻”对照表,不过他的“日夕分”总分爲十二,与《周髀算经》相同,比秦简十六分要少,又要取辰刻爲整数,因此误差较大。
宋王逵《蠡海集·历数》举出有以子、午、卯、酉各九刻,其余时辰各爲八刻,以及以子、午两时各十刻,其余时辰皆爲八刻等辰刻分配法[22]。王逵辰刻法是在百刻制前提下保证“一辰有全刻”所作的些微调整,可能与“日夕分”没有关係。
袁充辰刻法虽有保全整数刻的考虑,但基本上是太阳方位计时,以等距方位对应不等距时间,把方位角与时角区分开来。然而却招到李淳风严厉批评:“袁充素不晓浑天黄道去极之数,苟役私智,变改旧章,其于施用,未爲精密。”(《隋书·天文志》)在李淳风眼裏浑天家及其“黄道去极之数”才是正宗,袁充的地平方法是要不得的,精度也不合实用。然而李淳风未必能把时角与方位角区分开来,因爲在他稍后梁令瓒铸造浑仪,就把时间单位刻在地平圈(紘)上。
北宋熙宁七年(1074年)沈括上《浑仪》、《浮漏》、《景表》三议,其《浑仪议》曰:“(梁)令瓒以辰刻、十干、八卦皆刻于紘,然紘平正而黄道斜运,当子午之间,则日径度而道促;卯酉之际,则日迤行而道舒。如此,辰刻不能无谬。新铜仪则移刻于纬,四游均平,辰刻不失。”(《宋史·天文志》)梁令瓒的作法,错把方位角当时角;沈括将辰刻移于纬圈上,只考虑时角而不考虑方位角。象袁充那样既考虑方位角又考虑时角的辰刻方案实不多见。
袁充给出冬至“日夕分”对“昼夜刻”的数值结果爲4∶8对应40∶60;比秦简及《颛顼曆》的5∶11对应40∶60显得粗疏。这主要是由于袁充的辰法(十二)太小造成的。如果袁充改十二辰爲十六分,他将得到与秦简“日夕分”相同的结果。这也表明袁充所处的时代,人们对秦汉时期流行的“十六分”制已无所知。
秦简《日书》的冬夏至“日夕分”与秦汉地平式日晷上的六十九刻,是性质相同而又数值逼近的数据,据计算它们与北纬42°左右地区的日出入实际天象符合[23],相当于燕山至雁北一綫以北的草原地区。这与《尚书·尧典》所载“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云云,在季节与地理位置上大致吻合。
5 余论
秦简“日夕分”对应昼夜长短的理论值,可据现代天文学公式求出,据球面天文学关係,有:
sin Z sin A = cos δ sin t
式中冬至太阳赤纬δ= -ε,ε爲黄赤交角(随年代而有微小变化),取战国晚期公元前250年曆元,得ε= 23º.73;取天顶距Z = 90º.85(含蒙气差、太阳视差在内);冬至日入方位角按“日五夕十一”取A =180º×5/11=56º.25,代入上式,算得冬至日入时角:
t = 65º.25
化爲百刻制,得其冬至昼长约36刻,此即秦简“日夕分”对应的冬至昼长理论值。《四分曆》冬至昼漏四十五刻,实际代表日出日“昼长”40刻。因此秦简理论值比关中——洛阳(北纬35º左右)地区的冬至昼长约短4刻(合今约1小时)。这表明秦简“日夕分”的昼夜长短理论值,合北方草原地区(北纬42°)而不合中原地区(北纬35º)。
由此可见,所谓汉代施用的“秦之遗法”,包括秦简“日夕分”、《颛顼曆》漏刻法及汉人所谓古制、官漏等,是将北方草原地区的日出入方位,与中原地区的昼夜长短,杂糅在一起的混合体。
(编者按:[1]云梦睡虎地秦墓编写组:《云梦睡虎地秦墓》,文物出版社,1981年。
[2]于豪亮:《秦简〈日书〉记时记月诸问题》,中华书局编辑部编:《云梦秦简研究》,第351-354页,中华书局,1981年。
[3]《天水放马滩秦简·日书乙种》,转自张德芳:《简论汉唐时期河西及敦煌地区的十二时制和十六时制》,《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4]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甲种〈日书〉考述》,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编:《秦汉简牍论文集》,甘肃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7页。
[5]张德芳:《简论汉唐时期河西及敦煌地区的十二时制和十六时制》,《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6]曾宪通:《秦汉时制刍议》,《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4期;宋会群、李振宏《秦汉时制研究》,《历史研究》,1993年第6期;李解民:《秦汉时期的一日十六时制》,《简帛研究》第2辑,法律出版社,1996年;尚民杰:《从〈日书〉看十六时制》,《文博》,1996年第4期;宋镇豪:《试论殷代的纪时制度——兼论中国古代分段纪时制》,《考古学研究(五)——邹衡先生七十五华诞纪念文集》(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科学出版社,2003年。
[7]武家璧:《云梦秦简日夕表与楚曆问题》,《考古与文物》,2002年先秦考古专号,第318-323页。
[8](清)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第501-584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年。
[9]李鑒澄:《论后汉四分曆的晷景、太阳去极和昼夜漏刻三种记录》,《天文学报》, 1962年第1期。
[10]武家璧:《含山玉版上的天文准綫》,《东南文化》,2006年第2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发现陶寺文化大型建筑基址》,《考古》,2004年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城址祭祀区大型建筑基址2003年发掘简报》,《考古》,2004年7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汾市文物局:《山西襄汾县陶寺中期城址大型建筑ⅡFJT1基址2004~2005年发掘简报》,《考古》,2007年4期。
[12]全和钧:《我国古代的时制》,《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1982年总第4期。
[13]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天水市北道区文化馆:《甘肃天水放马滩战国秦汉墓群的发掘》,《文物》,1989年第2期;何双全:《天水放马滩秦简综述》,《文物》,1989年第2期。
[14]陈梦家:《汉简年曆表叙》,《考古学报》,1965年2期;又见《汉简缀述·汉简年曆表叙》,第248-251页,中华书局,1980年。
[15]张德芳:《悬泉汉简中若干时称问题的考察》,中国文物研究所编:《出土文献研究》第六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
[16]张德芳:《简论汉唐时期河西及敦煌地区的十二时制和十六时制》,《考古与文物》,2005年第2期。
[17]全和钧:《我国古代的时制》,《中国科学院上海天文台年刊》,1982年总第4期。
[18]宋镇豪:《试论殷代的纪时制度——兼论中国古代分段纪时制》,北京大学考古学丛书:《考古学研究(五)——邹衡先生七十五华诞纪念文集》,科学出版社,2003年。
[19]湖北省荆州市周梁玉桥遗址博物馆编:《关沮秦汉墓简牍》,第156-181简,中华书局,2001年。
[20]陈美东:《中国古代的漏箭制度》,《广西民族学院学报》(自然科学版) ,第12卷第4期,2006年。
[21]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第117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
[22]中国天文学史整理研究小组编:《中国天文学史》,第118页,科学出版社,1981年;一说王逵爲明初人,参纪昀:《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百二十三子部杂家类《说郛》。
[23]武家璧:《从出土文物看战国时期的天文曆法成就》,《古代文明》第2卷,文物出版社,2003年。 (责任编辑:admin)
原文出处:http://his.newdu.com/a/201711/05/514057.html
以上是关于八卦方位-论秦简“日夕分”爲地平方位数据的介绍,希望对想了解历史故事的朋友们有所帮助。
